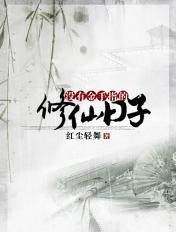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寒霜千年歌词 > 第293章 威压勋贵4000字(第2页)
第293章 威压勋贵4000字(第2页)
“动荡?”拓跋烬厉声道,“比起千万人无声死去,这点动荡算什么!林昭教会我的,不是如何做个好皇帝,而是如何让皇帝不必存在也能治国!”
数日后,念安一行抵达归仁城。他们在监察院门前静坐三日,拒不进食,只高举《民本录》残卷与婉儿带回的疫区照片??那些浮肿的脸、溃烂的手、枯瘦如柴的孩子,震撼朝野。
终于,拓跋烬下旨:革除潭州知府一切职务,押解进京受审;派遣太医院正使带队南下救灾;启用“紧急响应机制”,调动南方十二州医疗资源支援疫区;并诏告天下:“凡隐瞒疫情者,无论官职高低,一律以谋逆论处!”
大军开拔当日,念安登上长安城楼,遥望南方。烟雨茫茫中,他仿佛看见祖父骑着那匹青鬃老马,缓缓行于山道之上,背影苍老却坚定。
回到岭南,战疫已进入关键阶段。婉儿带领团队深入疫村,发现果然有人偷偷挖开了封堵多年的矿洞,企图盗采残余银砂。毒水再度渗入地下水系,酿成灾难。
她在村中连熬七夜,配制解毒汤剂,又指导村民重建双层暗渠。期间高烧不退,仍坚持施针救人。有人劝她休息,她只淡淡说道:“我祖父能走三十年,我能走三十年;我祖父能熬到最后一口气还在写字,我能熬到最后一滴汗流干。”
三个月后,疫情终被扑灭。朝廷追责数十名官员,其中不乏朝中权贵亲信。民间欢呼雀跃,称此役为“第二次乌溪胜利”。
然而风波未平。有御史弹劾念安“借祖荫擅权,干预朝政”,更有世家子弟讥讽昭明书院“收容贱民女子,败坏纲常”。甚至有人散布谣言,说林昭当年治疫实为试验邪术,导致多人成为“药傀”。
面对攻讦,念安不做辩解。他在书院墙上挂出一张巨幅图表,列出近十年岭南死亡率、粮食产量、识字率、水利工程数量的变化曲线,然后写下一句话:
>“数据不说谎。你们可以毁谤一个人,但无法推翻三千个村庄的活水渠。”
百姓看了,自发组织起来,在各地复制昭明模式。有的村子自建“小昭明学堂”,教孩子认字算数;有的乡镇成立“乡民议事会”,监督官吏用度;甚至连偏远苗寨也开始绘制自己的地形图,预防山洪。
启元二十年,新一代《宪纲》修订完成。其中明确规定:“教育权、医疗权、知情权为国民基本权利,国家须逐年增加投入,确保普及至每一个村落。”此外,还设立了“民本奖”,每年表彰一位像林昭那样默默奉献的平民志士。
这一年春天,念安站在祖父墓前,轻轻放下一本装帧精美的书??《民本录?终章》,由他历时五年续写完成。书中新增万余字,记录了林昭去世后的种种变革,以及普通人如何一步步改变命运。
“您说过,历史是由呼吸构成的。”他低声说,“现在,他们的呼吸,也成了历史。”
风吹过松林,沙沙作响,宛如回应。
多年以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来到乌溪。她是婉儿,已是八旬高龄,但仍坚持每年巡诊一次。她走过熟悉的渠边,抚摸刻着《防疫十策》的石碑,看着孩子们嬉戏奔跑,听着学堂里朗朗书声。
傍晚时分,她坐在林昭墓旁,掏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那是她少年时的听课笔记。翻开第一页,写着一句歪歪扭扭的话:
>“我要做一个能让别人活下去的人。”
她笑了,眼角皱纹如花瓣绽放。
夜幕降临,星辰满天。远处传来孩童的歌声:
>寒霜千年雪不开,
>一灯照破万重霾。
>老翁策马岭南去,
>换得春风入户来。
歌声飘向远方,越过山岭,穿过岁月,久久不息。
没有人记得所有细节,但所有人都知道:曾有一个老人,用一生点燃了一盏灯。那灯光微弱,却照亮了千万人的路;那灯光遥远,却温暖了千年的寒夜。
后来的人们常说,每当风雨如晦、人心迷茫之时,总会有人翻开《民本录》,轻声问道:
“如果是林夫子,他会怎么做?”
然后,便有人起身,走出屋门,走向田野,走向苦难,走向未知的前方。
就像当年那个白发苍苍的身影,执着地行走在岭南的山路上,不曾回头,也不曾停下。
寒霜千年,终有春来。
孤灯一盏,永照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