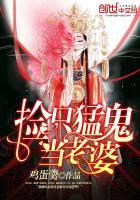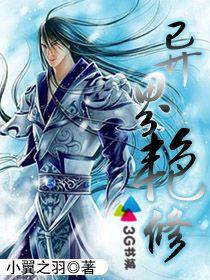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寒霜千年歌词 > 第297章 皇后的人照样杀(第1页)
第297章 皇后的人照样杀(第1页)
赵毅督前军,约五千人在他的本部。
左右两翼乃是护卫,各千余人。
不过并非全部都是作战部队,只有半数的兵员。
但左右翼和前军相隔只有不足十里,一旦发生危险,可以迅速策应,靠拢。
。。。
山雨欲来风满楼,乌溪的夏末却异常沉寂。蝉鸣稀落,田埂上无人行走,连平日最爱嬉水的孩童也都被大人拘在家中。自“明识令”推行以来,岭南各地学堂昼夜灯火通明,百姓争相传习辨伪之术,而那些曾靠蒙蔽乡民、篡改账册谋利的豪强,则如坐针毡。暗流涌动,风暴将至。
念安卧病已半月。高热不退,脉象浮虚,婉儿日夜守候,以银针渡气,汤药不断。阿岩每日从外带回消息,皆一一禀于床前。他声音压得极低,生怕惊扰病人静养,可念安每每在昏沉中听见关键词语,便猛然睁眼,冷汗涔涔:“战车?净水装置?……他们竟学得如此快。”
小满自京师归来探望恩师,带来一封密信??是陈骁亲笔所写,由禁军暗线递出。信中言:三藩虽暂敛锋芒,实则加紧联络旧部,更有一支伪装成商队的队伍,携大量“惠民药膏”北上,沿途赠予灾民。药膏气味清香,涂抹后确能止痛消肿,然经昭明分院化验,内含微量迷魂香,长期使用可致神志恍惚,易受暗示。
“又是记忆的侵蚀。”念安躺在竹榻上,目光穿透窗棂,望向远处雾霭笼罩的群山,“这一次,不是焚书篡史,而是用‘恩惠’换人心。比刀剑更狠,比蛊毒更悄无声息。”
小满跪坐在侧,双手捧着那本《寒霜纪事》,指尖微微发颤。“老师,我们该怎么办?不能再等朝廷反应了,等他们察觉,民心早已被窃。”
念安闭目良久,忽而轻笑一声:“你记得我教你识字的第一课吗?”
“记得。”小满低声答,“是‘人’字。你说,一撇一捺,相互支撑,才是人。”
“不错。”他缓缓睁开眼,“可若有人把‘人’字写成‘奴’,把‘公’字改成‘私’,你还看得出来吗?”
屋内一时寂静。婉儿端药进来,听见此语,手微微一抖,热汤洒出半盏。
“所以,”念安撑起身子,接过药碗一饮而尽,“我们要教所有人,不只是认字,更要懂得字背后的重量。”
次日清晨,念安强撑病体,在祠堂召集残存弟子与民间监察生代表共四十七人。他不再穿青衫,而是换上昭明书院老祭酒才有的玄色长袍,腰束铜环带,头戴素巾冠。这是他二十年未再穿戴过的礼服。
“今日不开讲,不授课。”他立于堂中,声如钟磬,“我要你们做一件事??回到你们出生的地方,去问十个普通人三个问题:第一,你最近吃的药是谁给的?第二,村口贴的告示是谁写的?第三,你小时候听的故事,和现在孩子唱的童谣,是不是同一个版本?”
众人面面相觑。
“这不是调查。”他继续道,“这是唤醒。真相不在卷宗里,而在一口井、一句歌、一场梦里。若十人中有三人答不上来,或答案前后矛盾,那就说明,寒霜又来了。”
他取出一枚铜印,交予小满:“这是我亲手刻的‘真言印’,凡你所录见闻,加盖此印,即为《寒霜纪事》续篇。不必华丽辞藻,只需如实记录。哪怕只写‘李家阿婆说今年的凉茶味道不对’,也值得记下。”
小满双手接过,眼中泪光闪动。
会议结束当晚,第一批“回乡问真”的队伍悄然出发。他们扮作游方郎中、货郎、戏班伶人,甚至乞丐,深入偏远村落。不出半月,各地回报陆续传回:
潭州某村,老人集体梦见“蓝衣郎中投毒”,醒来后拒服官府派发的防疫汤剂,宁喝山泉水致病;
越州一县学童齐唱新编童谣:“好官送药上门来,不吃便是忘恩人”,歌词竟与三日前分发的“惠民传单”完全一致;
更有甚者,婺源深山中的一个寨子,全村供奉起一座无名牌位,上书“救世清道公”,每逢初一十五焚香叩拜,香灰混入饮食,谓之“净心”。
念安读罢这些报告,整夜未眠。他在灯下重读陆知远的日记残页,忽然发现一行此前忽略的小字:“记忆可塑,信仰可造,唯恐惧最易引导。”他猛地合上册子,对婉儿道:“他没死透。他的思想,正在借‘善意’重生。”
阿岩怒不可遏,提剑欲北上刺杀三藩使者,被念安拦下。“杀一人易,破心魔难。他们不怕刺客,只怕百姓觉醒。我们要做的,不是流血,而是照亮。”
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百地辩真会”在南方拉开帷幕。由民间监察生牵头,每县择一集市,在正午时分设台开讲。不讲经义,不论政令,只做一事:当众试验。
有人带来“惠民药膏”,监察生当场取样,滴入特制试液,颜色由白转紫,证明含有致幻成分;
有人展示官府告示,监察生指出墨迹新旧不一,印章位置偏移,系伪造无疑;
更有老农牵出自家长猪,称其服用“免费饲料”后性情暴躁,监察生剖检其胃,发现残留粉末中含有兴奋类草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