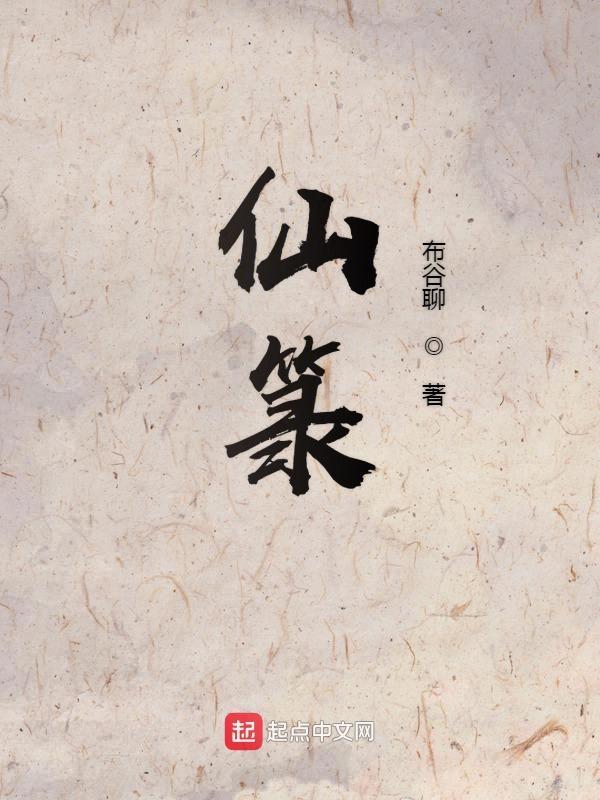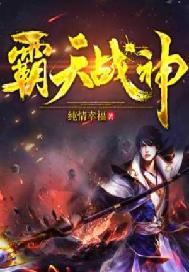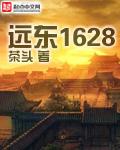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对弈江山全本txt > 第一千三百四十九章华夏好男儿岂能侍豺狼(第2页)
第一千三百四十九章华夏好男儿岂能侍豺狼(第2页)
岁月流转,人事更迭。曾经参与大战的老兵相继辞世,年轻一代对那段血火交织的历史只剩下模糊印象。有人开始质疑:那些关于木铃、忆族、情感共振的说法,是不是只是后人编造的传说?毕竟,如今再也无人见过发光的残片,也没有人能在梦中收到指引。
怀疑像野草般滋生。
直到一个名叫陆知的小吏,在整理档案库时发现了一份尘封已久的军报副本。那是百年前边关将领呈递给皇帝的密件,记录了一场诡异战役:敌军突袭之夜,我方士兵本已溃败,却在某一刻集体停步,放下武器,抱头痛哭。随后,他们开始背诵家乡童谣、呼唤亲人名字,完全无视战场指令。
报告最后写道:“……查无中毒迹象,亦无幻术痕迹。唯侦骑回报,当夜西北风起,夹杂不清歌声,似从地下传来。翌日清晨,战场遍地散落铜铃碎片,形制古老,非我朝所有。”
陆知浑身发冷。他翻遍史料,终于在一本残破地方志中找到线索:那片战场,正是当年木铃炸裂之地。
他连夜赶往当地,掘开荒土,果然在三尺之下挖出一片刻有铭文的铜片,上面写着:
>“勿忘吾妻生辰,八月初九,煮红豆粥以贺。”
他捧着铜片回到京城,将其置于回音坛中央,亲自诵读这段文字。当晚,数百里外的几个村庄同时出现异象:熟睡中的老人突然醒来,喃喃念叨起从未听过的生日祝福;几个素不相识的孩子在同一时间画出了同样的画面??一口锅冒着热气,锅边站着穿粗布裙的女人,桌上摆着一碗红豆粥。
陆知终于相信:记忆从未消失,它只是潜伏在时间的缝隙里,等待被重新唤醒。
他辞去官职,游历全国,收集散落的记忆碎片。无论是墓碑上的短句、旧衣里的纸条、还是孩童口中代代相传的童谣,他都一一记录。二十年后,汇集成一部《民忆录》,共三百卷,收录十万条普通人留下的痕迹。
他在序言中写道:
>“帝王将相,史书记之;功过是非,后人评之。
>唯有平凡之人,其爱其痛,常随肉身湮灭。
>今我所录,非为青史留名,只为证明??
>曾有人认真活过,被人深深记得。”
这部书后来被送入皇宫,皇帝阅毕,沉默良久,下令将其副本送往每一座忆学堂,作为必读教材。
又过了三十年。
桃林依旧繁茂,院子却被改造成一座小型纪念馆。四面墙上挂满了各地送来的纪念物:一双补了十七次的袜子、一封烧焦一半的情书、一只断了弦的琵琶、还有一块用指甲刻满名字的木板。
每日都有人前来祭拜,不是因为这里埋着谁,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这里是“记得”的起点。
某年春天,来了个流浪艺人,背着一把破旧三弦,衣衫褴褛,眼神却亮得出奇。他在院中坐下,调了调音,忽然开口唱起一首没人听过的新曲:
>“你说铃儿会响,是因为风吹,
>我却说,是因为有人想你。
>你说故事终会褪色,
>我却说,只要还有人提起,它就永远新鲜如初。”
歌声婉转,带着沙哑的深情,听得众人潸然泪下。一曲终了,有人问他:“这是谁写的?”
他笑了笑:“梦里有个老太太教我的。她说,这首歌本来就没有作者,谁唱出来,谁就是作者。”
说完,他起身离去,身影渐行渐远,消失在桃林尽头。
当天夜里,管理员发现供桌上多了一样东西??一把小小的泥塑三弦,旁边压着一张纸条,字迹稚嫩:
>“姐姐,这是我做的新乐器。你说过,音乐也是记忆的一种。我想让它替你说下去。”
没人知道是谁留下的。
但从那以后,每逢月圆之夜,馆内总会传出若有若无的琴声,不成调,却温柔得让人心颤。
时光继续前行。
一百五十年后,科技昌明,飞舟横渡长空,铁轨贯通南北。城市高楼林立,人们用晶石记录影像,能瞬间重现百年前的画面。有人得意地说:“现在再也不怕遗忘了,一切都能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