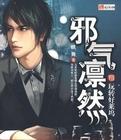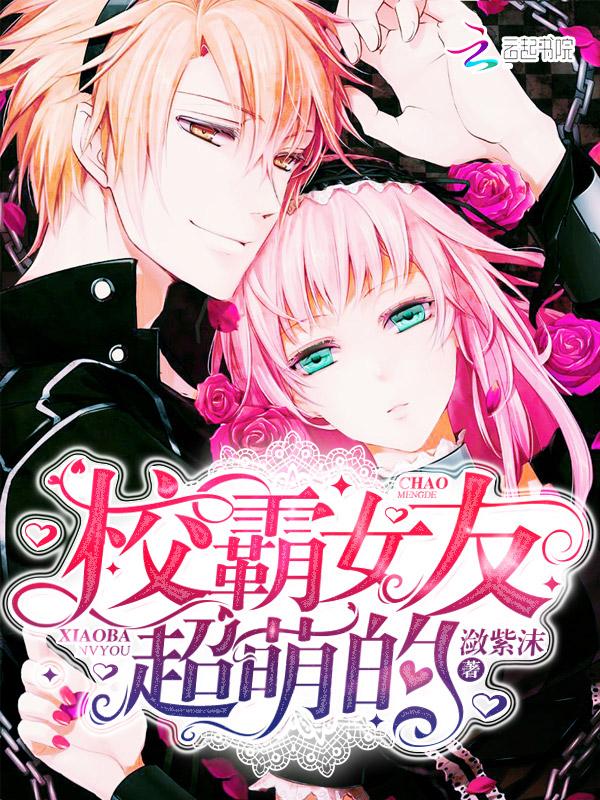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重工业之神 > 第61章 釜底抽薪解除危机(第2页)
第61章 釜底抽薪解除危机(第2页)
“人家区里的大领导,能看得上咱们?”
她的声音越说越小,最后几乎变成了蚊子哼哼,充满了自我否定。
果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信心,这是最大的障碍。
李向前语气平静,带著不容置疑的引导力。
“王厂长,为什么不行?”
他伸出手指。
“第一,我们有技术。”
“您忘了红星厂那台修好的1a616鏜床了吗?还有我们自己修復的非標轴承?这些都能证明我们的技术实力,不是吹出来的。”
王厂长嘴唇动了动,鏜床的事情確实让她脸上有光,但……
“第二,我们有產品。”李向前继续,“红星厂那么大的国营单位,下了正式採购单,这就是对我们產品质量最好的认可!这单子,就是我们的底气!”
“第三,我们能解决就业。”他指了指不远处正在干活的工人,“厂里这么多张嘴等著吃饭,项目做起来了,就能让更多人有活干,有饭吃。这正是区里领导关心的!”
他盯著王厂长的眼睛。
“有技术,有市场认可的產品,还能解决就业困难。王厂长,您告诉我,这三条,哪一条不符合区里要找的典型標准?”
王厂长被他一连串的反问问得哑口无言。
道理是这个道理,可……那毕竟是区领导啊。
她搓著手,焦虑地在原地踱了两步。
“可……可我们没人脉,不认识区里的领导,人家凭什么听我们一个小厂子的匯报?”
这是最现实的问题。
“这个您不用担心。”李向前胸有成竹,“我有个朋友,是报社的记者,叫林薇。”
“她消息灵通,而且认识区宣传部的领导。”
“我们可以请她帮忙,看能不能牵线搭桥,或者先写一篇內部参考的报导,把我们的情况反映上去,引起领导的注意。”
林薇的主动请缨,正好用在这里。体制內的事情,有时候需要巧妙的外部推力。
“记者?”王厂长愣了一下,隨即眼睛亮了些,“报社记者?那……那能行吗?”
“试试总比乾等著强。”李向前语气加重,“王厂长,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要么,我们被黄副主任用各种藉口拖死、整垮。”
“要么,我们主动爭取区里的认可和支持,拿到『试点单位』这块护身符。到时候,別说一个黄副主任,就是街道办主任想动我们,也得掂量掂量!”
他的话像锤子,一下下敲在王厂长的心坎上。
是啊,不爭,就是等死。
黄副主任那张不苟言笑的脸,还有那限期一周的威胁,又浮现在她眼前。
前进厂是她的根,是几十號工人的饭碗,绝不能就这么完了。
她看著眼前这个年轻人,比她儿子大不了几岁,却一次次在绝境中找到出路。
修机器,搞润滑脂,拿下红星厂订单,应付检查……
似乎只要有他在,天就不会塌下来。
她的心里天人交战,恐惧和希望在拉锯。
最终,那份对李向前近乎盲目的信任,以及求生的本能,压倒了长久以来的谨慎和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