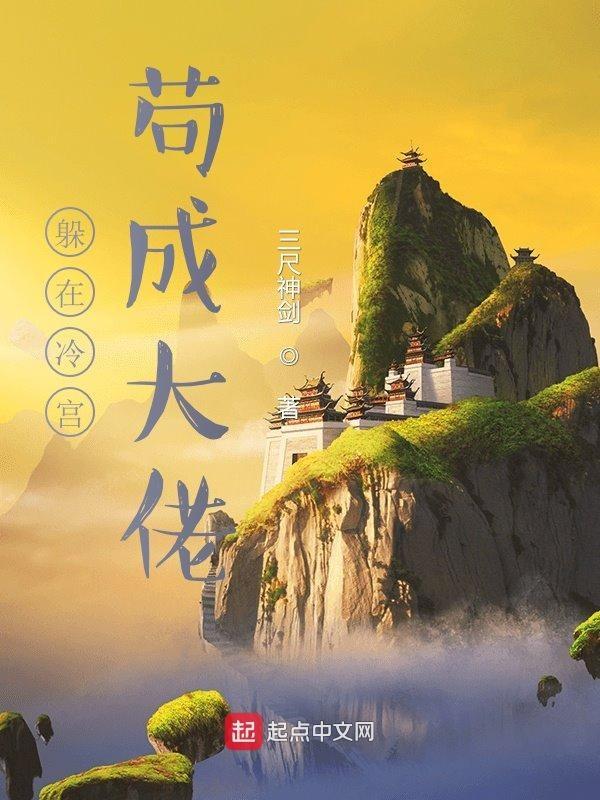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人间太岁神是水浒传中的谁 > 第三十二章 合家欢 下(第2页)
第三十二章 合家欢 下(第2页)
莫说洪元还不到收发自如层次,即便到了,一道柔劲打入敌人体内若不引发,也会成为无源之水,至多十几个呼吸就消散了。
劲力,终究也不过是自身气血之凝聚罢了。
黄少棠却不知这一点,也不感到有趣,脸上笑容比哭还难看:“洪兄,我错了,求你放了我吧。”
“你错哪儿了?”洪元饶有兴致说着:“这样吧,从现在到黄府,你想一百个你的过错,那我就饶了你。”
“洪兄……”黄少棠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哭?哭也算时间哦!”
黄少棠只好开始搜肠刮肚认错。
一路赶往黄府大宅。
洪元没有逼问黄少棠为何出卖他,那太苦情戏了,也无甚意义。
无非就是觉得科举路断了,这个‘朋友’没价值了,又或以往就存了嫉恨,现在不必隐藏了。
难道黄少棠真有什么‘苦衷’,‘不得已’之类,他就能放过不成?
眼下不过是猫戏老鼠以及借黄少棠身份入黄府罢了。
说合家欢就一定要合家欢。
洪元讨厌杀了小的,老的再没完没了报复的戏码,索性一步到位,直接送一个阖家富贵。
城东,荣庆巷。
黄府大宅,门前巨匾上镂刻着‘龟龄庄’三字,占地极阔。
此时黄府上下张灯结彩,虽是白日,各处却是灯火辉煌。
前院之内,宴开数十席,依然显得很是宽敞。
荣庆巷本就是清徐县诸多大户,官吏聚集之所,更有不少与龟龄堂有合作的外地豪客前来,院中自是喧笑之声处处,热闹非凡。
有那来得早的商贾就不由嘀咕:“不过是纳一小妾罢了,搞得这般隆重作甚?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娶正房呢。”
旁边有人搭话,轻轻做了个捻手指的动作,低笑道:“你知道什么?隔两年纳一妾,再办一场,光是收礼都收的盆满钵满,老哥儿,你送了黄老爷什么礼?”
“我……”
还不等这商贾回话,堂前响起一个高声唱喏:“张县尉到!”
霎时间喧声一滞,交谈声停了下来。
院中一众穿着得体的富商豪客,大户员外,财主吏员纷纷起身,聚到了门前迎接。
有客商心存疑惑,但也不敢造次,只压低了嗓音问道:“这张县尉何人?怎如此威风?这派头怕是连县令都比不上吧?”
“兄弟是外地人,第一次来咱们清徐县吧?”有人低声回答:“呵呵!我清徐县以张家首屈一指,十数代扎根于此,至于县令……”
这回答之人嗤笑一声:“我都快忘记他姓什么了,那位县令乃是天奉二年的进士,当了几年翰林官,后来下放至清徐……”
听了这话,不独是那客商,一些不明就里的人也都是会心一笑。
天奉七年停了生员廪饩,没几年天奉帝崩,今上登基直接一旨罢科举。
原本自百年前,大胤中枢就逐渐失去了对地方上的制约。
权力下放,州、府、县各级文武体系几乎尽被地方世家,豪族,军头,勋贵,大户所把持。
待得那一旨废除科举下来,就等于连大胤中枢都彻底摆烂了,几乎明摆着告诉地方上‘你们爱怎么玩怎么玩,老子不管了’!
那位清徐县令差不多都算最后一批科举官了。
这样的人到了地方上,毫无根基可言,既无实质上的权利,甚至连最后一点虚名都快丢光了。
能赢得了坐地虎才是怪事。
像张家这样的大户,钱粮充足,田亩商铺众多,经营着诸多产业,振臂一呼,随便就能拉出几百个敢打敢战的家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