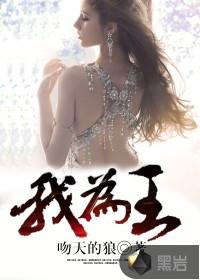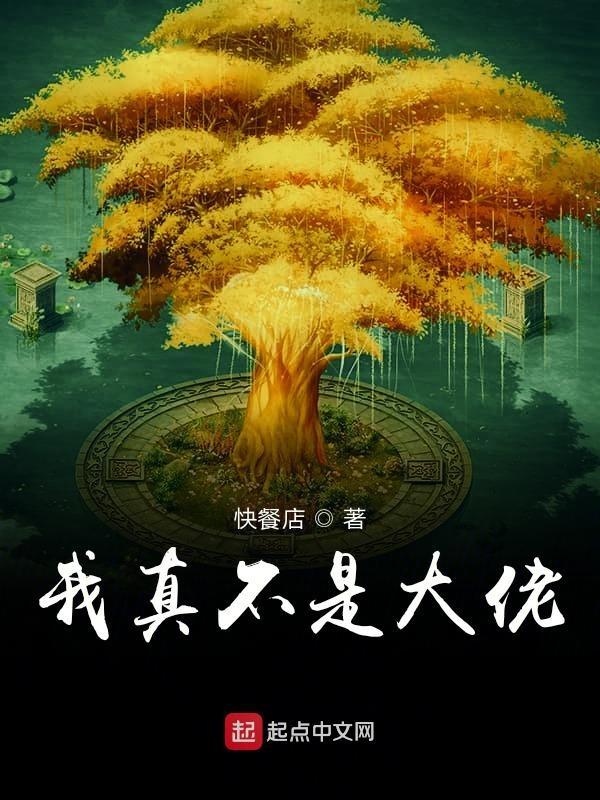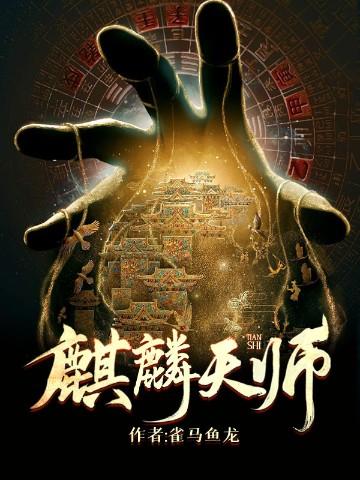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我是雍正的老婆 > 第221章(第1页)
第221章(第1页)
正月十五过了,朝堂诸官才算完全收敛起过年的懒散状态,投入到公事里。
通政使司此时也是一片忙碌状态。
“山东暴雪,压塌了不少房子,又该赈灾了,唉。”负责受理四方章奏题本的左参议向同屋的同僚抱怨了一句,“等初春雪化了,又是一场水灾,还得再赈。”
往日会附和他的右参议今日却是一言不发。
左参议看过去:“你干嘛呢,怎么不说话。”
右参议递过来一份题本:“你看这个。”
“是什么?”左参议边问边接过,先看人,立刻倒吸一口凉气,“嘶,怎么是他?”
再看内容,忍不住龇牙咧嘴道:“这是又要发疯了?”
看完后同情的塞给右参议:“辛苦你了,别担心,皇上不是迁怒的性子。”
右参议接过,皱眉道:“我倒不是怕被迁怒,只是感觉有些奇怪。”
“哪里奇怪?”
右参议摇摇头:“说不上来,就是感觉有些不对。”他把题本在手里磕了两下,道,“这个袁和裕,虽然一直很疯,但是、但是从来没有针对过……”
他竖起食指,往上指了指,又摊开题本看了看内容:“与他性子不符啊。”
左参议不以为然:“他有什么性子,不就是疯狗吗,逮着谁咬谁,好显得天下皆醉他独醒。估计是看针对怡亲王他们已经捞不到名声了,想搏一把大的呗。”
“希望如此。”右参议叹气,“唉,我就想安安分分办个公,他们这些大人,有事能不能直接上奏折给皇上,写什么题本送到通政司来多此一举。”
左参议撇嘴:“不送到通政司来哪能让大家都知道他干了什么呢,直接给皇上递奏折万一被皇上留中怎么办,岂不是什么都捞不到。”
两人一边吐槽,一边处理送到他们这里来的题本,处理完后呈给左右通政,左右通政再呈给通政使,通政使将左右通政汇总的条陈和重要的题本原件带着,去见弘书。
能送到通政司的题本,大多都是有章可循之事,因此君臣在一问一答中便将大部分题本都分好了去处,只待通政使回去与各衙门交接便是。
快结束时,通政使终于递上了袁和裕的那封题本:“皇上,这一封、可要分往都察院?”
弘书接过来一看,嗤笑:“劝谏朕的,都察院怎么处理,你也不怕左都御史去砸你家门。”
通政使尴尬一笑,他这不就是借个由头一说吗,难不成他还能说这一封您得自己处理。
“下去吧。”弘书将题本一放,也不说怎么处理,就开始撵人。
通政使明了,这是留中不发了,利落告退。出了门却没回通政司,而是脚步一拐,去都察院找左都御史孙嘉淦。
不久后,孙嘉淦亲自将他送出都察院,惹的都察院众人议论纷纷孙大人是吃错什么药了,竟然这般殷勤,莫非要为家中孩儿求娶通政使家淑女?
一向对朝中同僚不假辞色的孙嘉淦在下衙后,找上了张廷玉,开门见山:“张大人,皇上是不是要废除贞节牌坊?”
张廷玉被问的一懵:“何来此言?”
孙嘉淦满脸都是‘你不要与我装模作样’,道:“自皇上登基以来,还未赐下一块贞节牌坊,地方上的章奏,全部留中不发。”
张廷玉浅饮一口茶水,慢悠悠的道:“或许是国库不丰?皇上登基之后,连月天灾不断,皇上又是个爱民如子的性子,赈灾要求高不说,受灾地区的赋税也全部减免,万寿节都不曾大办,甚至为了省修玉牒的钱还免了天下避讳。一块贞节牌坊花费虽不多,但架不住人多,皇上心疼国库不是很正常。”
这例子举的太充分,孙嘉淦都忍不住怀疑了一下是不是自己太多虑了,但他可是御史头子,玩弄话术的祖宗,哪能被张廷玉几句话糊弄:“你莫要糊弄我,我虽不知国库几何,却还记得户部尚书年前笑开花的脸。”
张廷玉差点被茶水呛住,放下茶杯,叹道:“锡公,我真不知,皇上从未表露过。”
孙嘉淦狐疑的看着他,见他表情不似作伪,皱着眉勉强信了他,道:“那若皇上真有此意,你待如何?”
张廷玉反问:“那锡公你又待如何?”
孙嘉淦张了张嘴,复又沉默,良久,挣扎道:“自古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