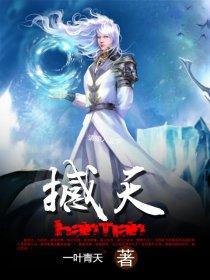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人在古代躺平开摆txt笔趣阁 > 第93章 九十三章 这样的诱惑摆在面前实在(第2页)
第93章 九十三章 这样的诱惑摆在面前实在(第2页)
他对解瑨道:“该给大嫂上柱香的。”
解三婶闻言,连忙道:“是了,虽说回头肯定还要带你堂兄弟他们来正式祭奠,但既然我们今日已经来了,不上一柱香说不过去的。”
她跟着解三叔站了起来,解瑨自然不会拒绝,众人一同到灵前给太夫人上了香。随后解三叔夫妻又同解桢一家三口以及徽音三姐弟各自见过,等一起用过饭,夫妻俩才离开了解府。
解三叔是同解瑨亲缘最近的一门亲,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解府来吊唁太夫人的客人络绎不绝。与解三婶说过的一样,解三叔又来了一回,这次带上了所有儿孙祭拜太夫人。
除了解家的族亲,当地知府、县令等等官员以及士绅也都各自上门,借机同解瑨结交这位可是简在帝心,板上钉钉的未来阁臣,交好总没什么坏处。
隔了几日,太夫人的娘家人也从隔壁的平阳府赶了过来。
来的人是太夫人的弟弟,即解瑨的舅舅,他身穿道袍,面相儒雅,半灰的长胡须修剪得十分整齐,一眼瞧上去便有仙风道骨之感。
解瑨的舅母早逝,舅舅未曾续娶,此番是独自前来,没有携带女眷,汤婵拜见过一次后便由着解瑨招待。
她手头的事情也不少,丧事宴请、管理内宅、照顾孩子……幸好有小于氏、福婶、还有紫苏等丫鬟这些能干的帮忙,人手充足,一切都很顺利。
就这样忙碌了小半个月,到了吉日,解家族人能来的都来了,解瑨同解桢亲自扶灵送棺,出城后走了十多里地抵达解家祖坟,将太夫人葬在了谢阁老身旁早早预留好的位置。
仪式过后,解三叔有事要找解瑨,解瑨回城后便到解三叔家坐了坐。
“我之前听大哥提过,守孝期间是朝臣养望的大好时机,”解三叔斟酌着问道,“如今丧事办完,这两年做什么,侄儿心中可有打算?”
解瑨颔首,“家父与家兄留下了不少治经的手稿,我打算将他们编纂成书。”
“编书?”解三叔闻言点点头,“嗯,编书确实不错,是个好主意。”
解瑨看出他像是有话要说,略一思索,想到什么,接着道:“若是需要,我也可以在闲暇时到族学,看看族中子弟的课业。”
“需要,自然需要!”解三叔听罢,立刻露出喜悦的笑容,目露欣慰,“哎,侄儿你也明白,咱们解家族学请来的董先生,有举人功名在身上,其实这样水平的先生,对于普通族学来说已经很是奢侈,但比起你来可就差远了你家学渊源,年纪轻轻便蟾宫折桂,又为官多年,不说董先生比不得,连府学的先生怕是都不如你……我已经打算交代在府学就读的几个解家子弟,定会让他们认真对待,哎呀,若是有你指点,可是那群小子的福气!”
他止不住高兴,一口气说了许多话,解瑨耐心听完,微微点头,“三叔放心,我既是解家一份子,自然要为解家出力。”
解三叔喜得合不拢嘴,跟解瑨仔细商议过教书的细节,才放解瑨回了家。
……
解瑨一进门,眼前就是熟悉的一幕
汤婵又在“欺负”解桓,也不晓得汤婵手里是个什么好东西,解桓想要,汤婵不给,抬着手让他蹦高伸手够,急得解桓小脸都快红了。
当地有习俗,送葬时女人家不好出面,汤婵正好留在家里躲懒。桓哥儿跟垚哥儿虽是男丁,但年纪太小,怕冲撞,也没有凑这个热闹。
孝期闭门谢客,也没什么娱乐,汤婵就只能逗孩子玩。
汤婵逗他就跟逗小狗似的,偏解桓不争气,对他百依百顺的奶娘丫鬟他嫌没意思,就爱跟汤婵玩闹,解瑨发现这一点之后,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见到父亲回来,解桓才不情不愿地停下,给解瑨行礼,“见过父亲。”
在汤婵这儿越久,桓哥儿是越来越不怕解瑨了。
解瑨沉默一会儿,低头看着他,“你如今已过三周岁,若按虚岁,已有五岁,该开蒙了。”
“开蒙?”
解桓还没反应过来这是什么意思,汤婵先惊了一下,“他才萝卜头一点大,就要开蒙了?”
这下解桓不高兴了,撅个嘴不满地看向汤婵,“不是萝卜头!”
汤婵暼了一眼解桓,故意道:“你还没我膝盖高呢,不是小萝卜头是什么?”
解桓憋气,大声道:“我不是萝卜!”
汤婵哄他,“好好好,那咱们桓哥儿是小土豆。”
解桓t?一愣,表情疑惑,“土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