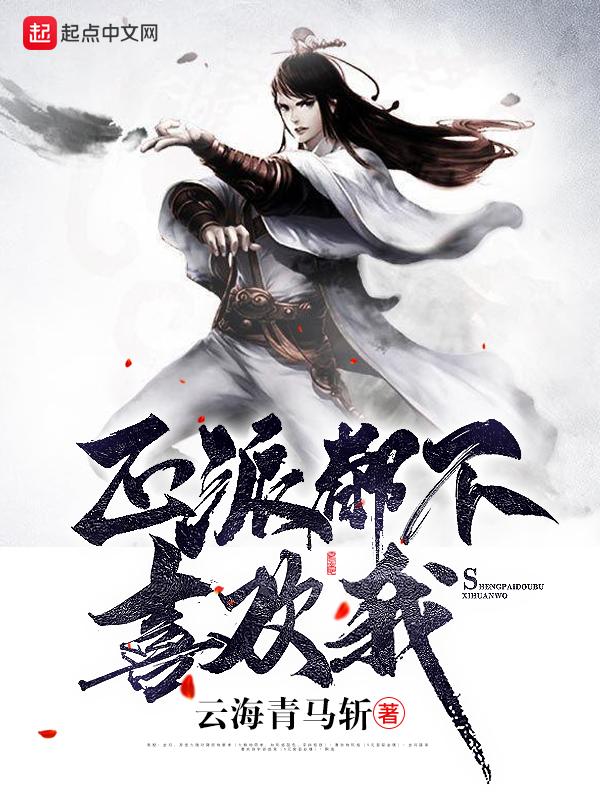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钢铁是如何炼成 > 北境(第1页)
北境(第1页)
“你是说用铁范?”钟应道。
苏冶摇头,抬手虚指向炉身一侧,“非是制作铁器的范具,而是与炉身相接的通道。”
钟应蹙眉思索片刻,眼中露出明了之色。
“第一批铁烧成后,由管道而出,不待炉内冷却便添矿料,继续烧制?”
钟应到底有经验,条理清晰。
苏冶点头,“正是。”
不曾想钟应默了片刻后,却是摇头。
苏冶见他神色凝重,不由问道:“可是有什么不妥?”
钟应略作迟疑,还是说道:“浇注通道不似风箱,于这炉子而言,不易改制,况且先前此炉新搪,怕是不便再动。”
苏冶知道他的意思——这炉子缝缝补补动得太多,再动怕是要废掉。
但她心里早有成算,便道:
“倘若这炉就起这最后一次呢?”
钟应闻言一怔,抬眼看向苏冶,目光中带着几分讶异。
苏冶不慌不忙,继续道:“官窑的大鉴炉时常连起百日,百日后炉体破败,便弃旧置新。”
她边说边将手轻覆在炉身上。
“这炉子我至多保它三十日不败,三十日炉火熄灭,便得置新炉。”
她转目看向钟应,语气沉静:
“但您也应能算清这笔账,炉火三十日不败,省下的炭料、增余的出铁,与置新炉的钱相比,孰轻孰重?”
钟应闻言,捋须沉思片刻,末了,开口道:
“怎知曹兄弟愿意购置新炉?”
苏冶笑道:“因为钱。”
钟应自然明白这笔账他能估量,若这炉火三十日不败,置新炉的钱同炭料和出铁量相比,着实不值一提。
“此事可知会过曹兄弟?”钟应道。
苏冶摇头:“只告诉过他续炉之事。”
钟应哑然,敢情这丫头竟是只拣好处说。
“你是要来个先斩后奏。”
苏冶并不否认,“横竖是往他腰包里塞银子,用什么法子无甚要紧。”
钟应道:“你怎知我不会同他讲?”
苏冶转头看他,严重含笑:“钟师傅是个明白人,告诉曹经,他若瞻前顾后,贪眼前小利,未必放得下心,只要能赚银子,何必事事知会,末了,钱落进大家伙儿腰包,自然无人计较来处。”
钟应未再接话,只凝目看向炉子,良久,叹了口气。
“既如此,便请人给这炉子加浇注。”
“不必。”苏冶即时应声。
钟应神色诧异地看向她。
苏冶解释道:“我来便可,三日内便能落成。”
若是从前,钟应大抵会觉着她是口出狂言,但经历了搪炉、烧铁诸事,他多少知晓她手段非凡,只忍不住问道:“你当真只是年幼时在你父亲身边学过些?”
苏冶笑道:“我自小天资聪慧,过目不忘,这冶铁的事宜,只要过上一眼便知晓门道。”
她这话五分真五分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