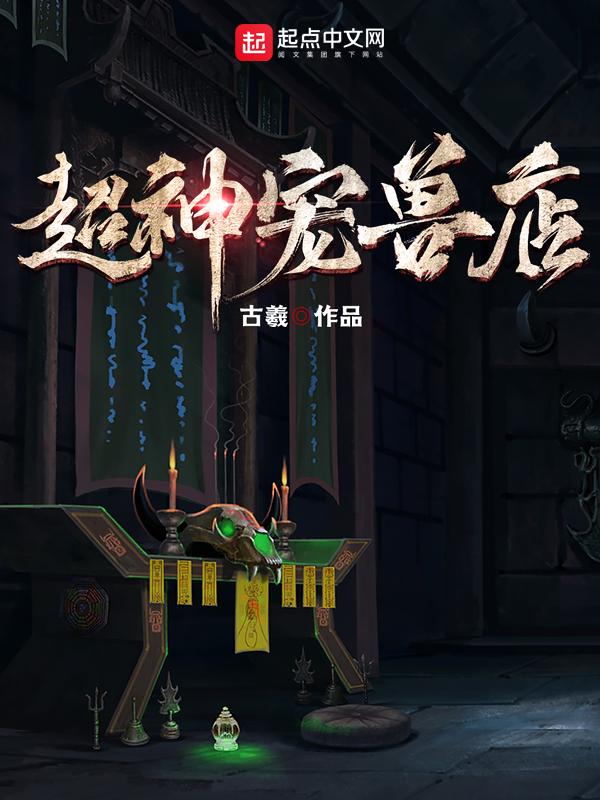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天未明是什么意思 > 第三十七章 墨阵隐杀机(第1页)
第三十七章 墨阵隐杀机(第1页)
程岩摔门而去的巨响,如同重锤砸在凝滞的空气上,余音在狭小的西厢房内嗡嗡作响。苏云岫紧握着冰冷的勃朗宁模型枪,指关节因用力而泛白,几乎要嵌进硬塑枪柄里。方才那番淬冰般的质疑,那毫不掩饰的敌意,像细密的针,狠狠扎进她刚刚建立起些许信心的心房。她挺直的脊背几不可察地颤了一下,眼圈瞬间涌上热意,却被她死死咬住下唇,倔强地逼了回去。这份被当众质疑的屈辱感,远比在76号受训时任何皮肉之苦更令她难堪——她渴求的是认同,是归属,而非这冰冷的尖刺。
沈曼笙无声地叹了口气,温热的掌心带着抚慰的力量,轻轻落在苏云岫紧绷的肩头。“别往心里去,云岫,”她的声音温和却带着磐石般的沉稳,目光投向那扇隔绝了程岩怒火的房门,“程岩他就是块爆炭,一点火星就能燎原。这些年,他见过太多披着羊皮的狼,也亲手埋葬过被‘自己人’背后捅刀子的兄弟。那血淋淋的教训,是刻进他骨子里的疤。所以对任何靠近核心的‘新人’,他那身刺,总是先竖起来再说。他对七爷,对组织的忠诚,毋庸置疑,只是这表达……”她无奈地摇摇头,“太糙了些。给他点时间,也给你自己时间。”
一旁的钱益民已将擦拭好的手枪部件一一归位,动作一丝不苟,如同老匠人侍弄珍品。他推了推滑至鼻尖的老花镜,浑浊却异常清明的目光透过镜片,落在苏云岫脸上。那目光仿佛能穿透她内心的波澜,声音低沉沙哑,带着岁月沉淀的从容:“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苏姑娘,心定则神凝。把你该做的,能做的,做到极致。是非功过,时间自会评说。”他顿了顿,语气更显深沉,“疑云遮眼时,低头看路,莫问前程。路走稳了,信你的人,自然会跟上。”
苏云岫深深吸了一口气,那空气中仿佛还残留着程岩的怒火与药油的气息。胸中翻涌的酸涩和委屈,被沈曼笙的宽慰和钱益民这充满智慧的点拨强行压了下去,化作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她用力点了点头,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却异常清晰坚定:“沈姐,钱老,我明白。我会用行动证明自己。”不再看那紧闭的房门,她重新握紧那把沉甸甸的模型枪,将所有的专注、所有的决心,都倾注在沈曼笙的指导下。拔枪、抬臂、三点一线瞄准远处廊柱上一个微小的木疤、屏息凝神、收枪入套……动作一丝不苟,比之前更加沉稳流畅,每一次重复,都像是将心中的杂念与不安一同锤炼出去。汗水再次浸湿了她额角的碎发,顺着细腻的脖颈滑落,然而她的眼神,却如同被反复淬炼的寒星,愈发清亮锐利。
同一时刻,霞飞路那座被梧桐温柔环抱的花园洋楼内。
陈默群难得兑现了一次承诺。午后的霞飞路,“霓裳”绸缎庄内,暖阳透过巨大的玻璃橱窗,映照着琳琅满目的绫罗绸缎,空气里弥漫着新布料的淡淡馨香。林晚脸上带着久违的明媚笑意,像一只终于被放出笼子的金丝雀,兴致勃勃地在色彩缤纷的布料前流连。陈默群陪在她身边,金丝眼镜后的目光看似温柔宠溺,实则不动声色地扫视着店内每一个角落和进出的人流。
“默群,你看这匹湖蓝色的软缎怎么样?给我的洋娃娃做条新裙子,一定很衬她金色的头发!”林晚拿起一匹闪着柔光的缎子,比在自己身前,回头雀跃地问。
“好,晚晚的眼光当然好。”陈默群含笑点头,随手示意店员将那匹料子包起来,目光却掠过林晚的肩膀,落在门口一个刚进来的、穿着半旧藏蓝布袄、挎着菜篮子的中年妇人身上。那妇人面容普通,带着市井的沧桑感,目光有些畏缩地扫过店内华丽的陈设,似乎被价格吓到,只敢在门口摆放打折布料的区域小心翻看。
林晚又拿起一匹藕粉色的素锦,正想询问,旁边一个抱着几匹厚重呢料、似乎急着去库房的店员脚步匆忙,不小心蹭到了林晚的胳膊肘。林晚“哎呀”轻呼一声,手中的素锦滑落在地。
几乎是同时,那个在门口看布料的蓝袄妇人,像是被身后的顾客挤了一下,一个踉跄也向前扑倒,手中的菜篮子脱手飞出,里面的土豆、青菜滚落一地,正好有几颗滚到了林晚脚边。
“对不起!对不起小姐!您没事吧?”店员慌忙道歉,弯腰去捡那匹素锦。
“哎哟!作孽啊!我的菜!”蓝袄妇人带着浓重的外地口音,手忙脚乱地在地上摸索着捡拾滚落的土豆,显得狼狈又笨拙。
场面一时有些混乱。陈默群的眉头微不可察地蹙了一下,目光锐利地扫过那笨拙的妇人和店员,确认只是意外,才伸手扶住林晚,温声道:“没事吧晚晚?没碰着吧?”
林晚摇摇头,目光却被脚边一颗滚过来的土豆吸引了——土豆下面,压着一小片折叠得异常工整的、边缘被撕得毛糙的纸条!它显然是从那妇人慌乱中掉落的什么东西里散出来的。
就在林晚弯腰想去捡那颗土豆的瞬间,那蓝袄妇人已经手快地将土豆连同下面压着的纸条一把抓起,胡乱塞回菜篮,嘴里还不住念叨:“对不住啊太太,对不住,乡下人笨手笨脚……”她低着头,匆匆将地上的菜捡回篮子,甚至没看林晚一眼,就挤开人群,逃也似的离开了绸缎庄。她的动作看似慌乱笨拙,但捡起纸条塞回篮子那一下,却快得如同错觉,纸条的边缘似乎在她粗糙的指缝间一闪而过。
陈默群的注意力被妇人的离去和林晚是否受伤吸引,并未留意那张小小的纸条。店员捡起素锦,连声道歉。林晚的心却怦怦直跳,刚才那惊鸿一瞥,纸条上似乎有几个潦草的字迹……
“晚晚?”陈默群的声音将她拉回。
“啊?没……没事。”林晚强自镇定,挤出一个笑容,“就是吓了一跳。我们……再看看别的?”
回到那座精致却压抑的花园洋楼,林晚借口试新布料需要安静,将自己关在卧室里。她反锁上门,背靠着冰凉的门板,心脏仍在狂跳。她颤抖着从贴身的口袋里,摸出那张在绸缎庄混乱中,她趁着所有人都没注意,飞快地从妇人刚捡起土豆和纸条、还未完全塞进篮子时,用指尖极其灵巧地“拈”过来的小纸条!
纸条被汗水微微浸湿,边缘毛糙,显然是从某个本子上匆忙撕下的。上面用铅笔潦草地写着几个字,力透纸背,带着一种急促的警示:
白玫瑰
囚笼
没有落款,只有这触目惊心的两个词!
林晚如同被一道冰冷的闪电劈中,浑身僵硬!白玫瑰……那是默群温室里精心培育、永不凋谢、象征着他“永恒爱意”的花朵!囚笼……这张纸条,像一把冰冷的钥匙,瞬间捅开了她心底那扇被重重疑虑锁住的门!
她猛地冲到梳妆台前,拿起那个精致的珐琅彩胭脂盒,又看向梳妆镜中自己苍白却难掩惊惶的脸。夕阳熔金,透过宽大的落地窗,在她身上投下长长的、寂寥的影子。指尖无意识地划过光滑冰凉的台面,这张神秘出现的纸条,如同投入心湖的巨石,激起的涟漪在她心中疯狂扩散、撞击着堤岸。
默群对她,似乎真的无可挑剔——昂贵的珠宝、应季的巴黎时装、永不凋谢的白玫瑰……他用无尽的物质和看似无微不至的温柔,为她精心构筑了一座梦幻的堡垒。然而,“无微不至”的关怀,早已在她心底织成了一张无形的网。
他不喜欢她过多接触外界。每当她兴致勃勃地提起想出门访友,或是参加某个慈善茶会,他总有充分的、不容反驳的理由婉拒——“外面太乱了,晚晚,我不放心”,“那些人配不上和你交往,乖,在家画画弹琴不好吗?”;他从不让她触碰他工作的边角。若她好奇地、小心翼翼地提起“76号”,他镜片后的眼神总会瞬间变得幽深难测,如同寒潭,随即巧妙地用一个温柔的吻或一件更名贵的礼物,将话题轻飘飘地转移开;他甚至会“不经意”地、用闲聊般的语气询问她每天读了什么书,见了什么人,语气温柔依旧,却总带着一种让她无法忽视的、审视猎物般的锐利。
“白玫瑰……囚笼……”林晚的手指死死抠紧了冰凉的窗棂,指尖因用力而微微泛白,纸条在她掌心被攥得皱成一团。楼下花园里,那个沐浴在金光中的白色秋千架,此刻在她眼中,那优美的弧线仿佛扭曲成了冰冷栅栏的形状——它不再象征浪漫与自由,反而像一个精致绝伦、镶着金边的巨大鸟笼。她这只被精心喂养、用爱之名呵护的金丝雀,真的快乐吗?默群……这个她曾深信深爱着自己、自己也倾心相付的男人,他华丽长衫下包裹的,究竟是怎样的一颗心?他温和笑容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令人心悸的秘密?
那个在绸缎庄笨拙的蓝袄妇人……那惊惶的眼神,那粗糙的手指……她是谁?为什么要冒着如此风险传递这样的信息?这张纸条,是警告?是求救?还是……为她打开牢笼的一线生机?
一个念头,如同黑暗中疯狂滋生的带刺藤蔓,带着冰冷的触感和灼热的渴望,紧紧缠绕上她的心房,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几乎让她窒息:她必须知道真相。哪怕这真相只有一丝微光,哪怕它可能将她精心构筑、赖以生存的整个世界彻底击碎,也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