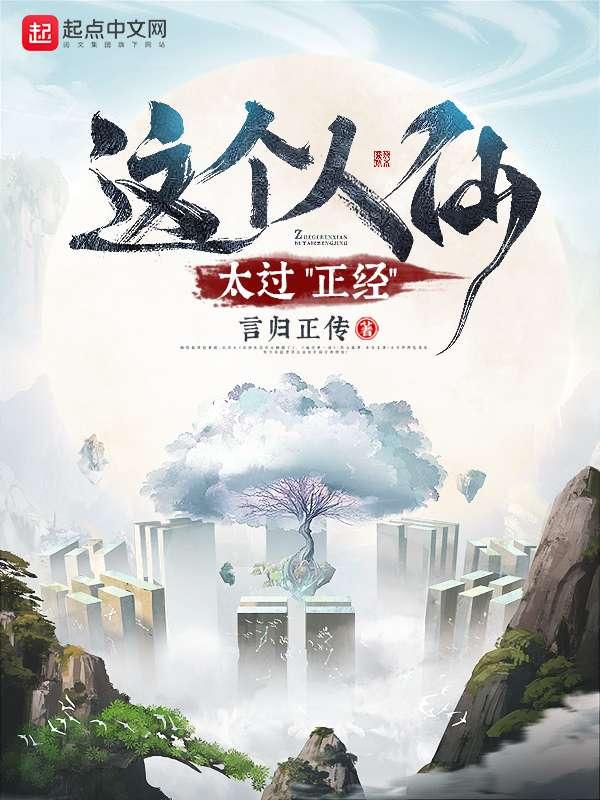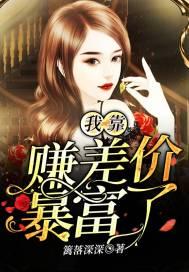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我用美食征服npc > 商会质询(第1页)
商会质询(第1页)
用油纸包好的桃片,正整齐堆放在药铺门口的柜台上。与往日不同,每一袋桃片上还用细麻线捆了一张拜年飞帖,上书“桃片且备,腊酒盈盅”*,下落款“景和”二字。
飞帖是梁夏朝拜年送福所用,后世的贺卡便是其遗风。尽管是个小作坊,沈畔也要给客人足够的仪式感。
之前沈畔灵机一动推出的“巴郡特产”,比她想象中更受欢迎。
半月前,她和胡有良就不卖肉夹馍了,把屠宰房的后院收拾出来,除了出摊便在那里专心做桃片。即使如此,景和桃片仍旧供不应求,一出摊便大排长龙,不到两个时辰就售空了。
毕竟糖价不低,赚钱首先要图个餐饱,甜品那是偶尔才会尝鲜。
但一包景和桃片才售十文,软糯清甜,还十分柔韧,薄薄一片却绕指不断,连走十日水路到家都无碎渣,无论是带回家给家人尝鲜,还是路途中当做零嘴,都是极好的。
一时间,卖"巴郡特产"的小摊前时时刻刻都围满了人,甚至堵住了通行的道路。沈畔没法,只能和路旁的药铺做交易,付租金,只在他们空闲的时候借用铺子两个时辰。
这一借用,便有传言说景和桃片不仅好吃,还有药用功效,养生健体。
纵使沈畔每次听到都尽力解释,流言也已经随着商船漂去了梁夏朝的大小郡城。
门口已经有些人在排队候着了,药铺的孙大娘见他们过来,笑呵呵地招呼:"今日怎么这么晚?有好几个急着赶船的客人,说要是买不到回去娘子一定责骂,我就自作主张替你们开张了。"自从把铺子租给他们卖景和桃片,孙大娘店铺人流如织,连带着药材都好卖,她便十分地乐成其见。
“孙大娘,这也太麻烦你了!”沈畔赶紧去接过孙大娘手上的活,心里愈发感叹,她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手实在不够。
最近琐事缠身,年前牙人也少,找帮手的事一直搁置着。
队伍越排越长,沈畔一边和客人攀谈,一边打算盘收钱。
突然,人群中传来一阵喧闹。
那阵喧闹愈发靠近,把排队的人都冲散了。一名书生模样的锦衣男子领着十几个高个男子,把店门口围住了。
他们没穿官府的衣服,沈畔摸不清底细。
孙大娘此时凑过来,在她耳边低声说:“为首的那个巴郡商会的乡绅陈生,是商会司事的西席。”
陈生是是秀才出生,多年考举人而不中,又自认半只脚踏进了官府,不愿意去给小儿开蒙,一来二去,就被商会吸纳了。虽说近年来巴郡官府对商会的倚仗程度愈深,可商人地位不高,他便正好作为商会行事的代理,还算有些声望。
陈生留着长须,目光洞察如炬,可惜身形有些臃肿,让他少了儒雅,多了些市侩。
“官爷,您看看,我们好好做生意呢,您这是。。。。。。”沈畔试探着开口。
陈生被这一声“官爷”叫到心坎里,面上仍旧不动声色:“报上名来。”
沈畔迟疑着,胡有良说话了:“官爷,我是西巷屠宰房的,我叫胡有良,是个屠夫,这是我的远房侄女沈畔。”
陈生瞧着这个水葱似的少女,和鱼龙混杂的格格不入的模样,总觉得有几分眼熟,但怎么都想不起来,只好接着说道:“屠夫?平日在哪里做营生?”
胡有良反应过什么似的,回答得有些艰难:“平日。。。。。。我们在码头上摆摊,没有固定的地方。”
“那么情况已经清楚了,按照商会的规矩,你们已经构成了扰乱经商秩序,以次充好。”
“怎么就以次充好了!我们做错了什么?”胡有良急了。
“既然你如此好学,我就跟你讲讲。”陈生拿起包桃片,放在手上掂量:“商会规矩,你卖什么都要先来登记造册,批准后方能售卖。你这东西登记了吗?没登记的东西,难道不是以次充好,扰乱市场?”
“这。。。。。。这。。。。。。从来都是店铺才需要登记,我们不过就是摆摊的而已。。。。。。”胡有良被这一通话压低了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