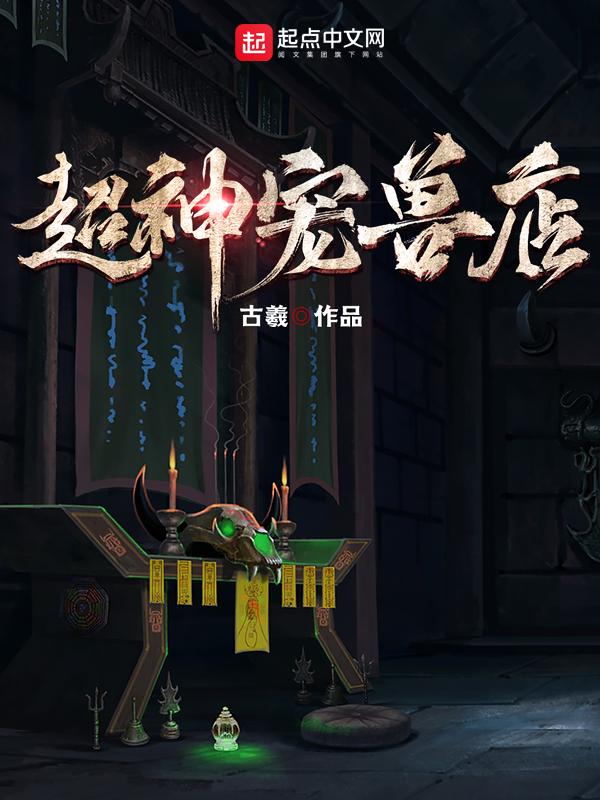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棺材铺的老板娘笔趣阁 > 第 6 章(第1页)
第 6 章(第1页)
陈青禾从来没想过自己居然能和陆明远达成同盟。
陆明远算是她见过的,第一个为女性发声的男人。
经历了刚才的对话,好像他们两个刚开始见面的剑拔弩张在一刻莫名的消散了,双方不约而同的达成了共识。
陈青禾弯腰捡木棒时,袖口蹭到地上的桐油,黑黢黢的黏在青布衫上。
陆明远忽然伸手,指尖捏住她袖角被油浸透的布:“这料子不经蹭。”他的手虽凉,但稳得让人安心。
陈青禾抬头,正撞进他眼底的光,那光不是热的,却也能把人心里的冰碴子慢慢焐化。
陈青禾下意识要抽回袖子,陆明远却先松了手,拐杖在地上轻扣一声,“上个月,刘老栓拿着一个玉扳指来当,说要换五十两银子。”他扯了扯嘴角,眼尾微挑,“那扳指是他侄媳妇的丈夫给的。”
陈青禾的手指无意识地绞着木棒,她轻叹了一声。
“我查过,刘老栓欠了三百两。”陆明远的声音沉下来,“催债的放话,再还不上就卸他一条腿。”
话音顿了顿,他忽然抬眼,“你在棺底凿了个暗格,里面放了木刻像,对不对?”
陈青禾猛地抬头,眼底闪过惊讶:“你怎么知道?”
“我看过那口棺材。”陆明远笑了,意有所指的比了个手势。
“你在棺盖上刻了朵极小的梅花,是给死者的记号。”
陈青禾伸手拍了拍手上的脏污:“你倒是看的仔细。”
“你给死人刻梅花的记号,我给活人记贪腐的账。”陆明远转身要走,又回头看她,“也算合作愉快。”
后堂传来脚步声,柱子抱着新刷了朱漆的棺材走出来,二栓跟在后面,手里举着块新写的牌位,纸角被风掀起一角,露出个歪歪扭扭的“刘”字。
“刘家嫂子叫春枝。”
陈青禾接过牌位,指尖在"刘"字上顿了顿,到底没改,只把牌位塞进二栓手里,“记牢了,往后上香时喊全了她名儿。”
二栓点头,攥着牌位和柱子一起出去了。
陈青禾站在原地,看着陆明远拖着那条僵硬的腿挪出门去。
夕阳斜斜切进门槛,在他肩头镀了层金边,那点义肢磕碰青砖的细碎声响,很快便被穿街而过的晚风揉散了。
当天夜里,雨来了。
不是淅淅沥沥的小雨,是憋足了劲的瓢泼大雨。
豆大的雨点砸在铺顶的瓦片上,噼里啪啦的。
陈青禾裹着薄被坐在榻上,听着外面鬼哭狼嚎的风雨声。
额角的伤口在湿冷的空气里隐隐作痛,脑子里却一遍遍过着“速装棺”的榫卯结构图。
那是她爹当年琢磨出来的玩意儿,暴雨天抢时间入殓用的,她接手铺子后改良过几次,榫头更小更密,滑槽也开了暗扣,只是……一直没机会真正派上大用场。
雨越下越大,砸得人心烦意乱。
就在她以为这鬼天气不会有人上门时,铺门被擂得山响!
“开门!陈掌柜!救命啊!开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