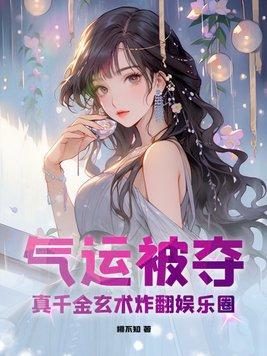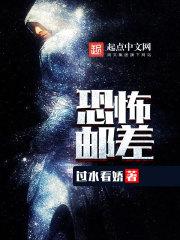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太子竟然暗恋我 > 柳成(第1页)
柳成(第1页)
济世堂的檐角,不知何时结了层薄霜。
“姑娘,太子殿下的马车在门口呢。”小石头捧着药筛进来,鼻尖冻得通红,“他说……说带您去城西查那咳血的案子。”
左忆正用镊子夹着片干枯的曼陀罗花瓣,闻言指尖顿了顿。昨日李承恩留下的卷宗她看了半夜,死者是个绸缎铺的掌柜,姓周,三十五岁,无妻儿,独自住在铺子里。仵作的记录潦草得很,只写了“寅时发现死于卧房,口吐鲜血,身无外伤”。
“把验尸用的银针和瓷盘装起来。”她把曼陀罗花瓣收进药盒,声音平稳,“再带瓶米醋——若真是毒物,或许能测出些痕迹。”
小石头应着去了,陈嬷嬷却端着件厚披风进来,往她肩上搭:“深秋的风刮得跟刀子似的,披上吧。殿下特意让人来说,城西郊外冷,让你多穿点。”
披风是灰鼠皮的,里子衬着浅绿的绸缎,针脚细密,显然是新做的。左忆摸了摸领口的绒毛,忽然想起昨日李承恩碾苍术时,指尖沾着粉末的样子——他那样的人,竟会留意这些琐碎事。
“不过是查个案子,不必这么讲究。”她想把披风摘下来,却被陈嬷嬷按住:“殿下的心意,你得接着。再说,冻着了怎么试药?”
正说着,门帘被风掀起,李承恩站在门口,身上裹着件墨色的狐裘,见她披着灰鼠皮披风,眼底先漾开点笑意:“倒是合身。”
他身后跟着个侍卫,捧着个黑漆木盒,打开来,里面是套银制的小工具:镊子、探针、小巧的剪子,打磨得锃亮。“陈嬷嬷说,你查案用得上这些,比银针方便。”李承恩指着那剪子,“剪布料用的,不会伤着手。”
左忆拿起那把小剪子,银柄上刻着细密的云纹,握在手里竟不冰,想来是被人焐过。她抬头看他,见他耳尖又有些红,像是怕她拒绝,便低声道:“多谢殿下费心。”
“该谢你才是。”他侧身让她出门,“这案子牵连甚广,周掌柜手里握着不少官员的绸缎账,大理寺查了三日,半点眉目也无。”
马车里比外面暖得多,角落里放着个黄铜暖炉,炭火燃得正旺。左忆刚坐下,李承恩便递来个锦袋,里面装着几块姜糖:“路上风大,含块糖暖身子。”
左忆皱着眉接过,她有些搞不清李承恩这几日的温柔关怀,仅仅是帮他查清了容妃的旧案?
她捏起块姜糖,糖纸是描金的,印着缠枝莲纹,和那日穿的月白襦裙上的花样很像。糖块放进嘴里,辛辣的姜味混着甜,倒真驱散了些寒意。
“周掌柜的绸缎铺,听说专供官场?”左忆拿出卷宗,借着车帘透进的光细看。
“嗯,不少官员的官服料子,都从他那里订。”李承恩的指尖点在卷宗上的“账册”二字,“大理寺的人说,他卧房里的账册不见了,像是被人刻意拿走的。”
左忆皱眉:“若真是为账册杀人,为何要做得这么张扬?咳血而亡,一看就不像急症。”她忽然想起前世见过的砷中毒案例,死者也会呕血,指甲缝里常留着细微的白色粉末。
马车在城西的绸缎铺前停下。铺子关着门,门环上挂着把铜锁,锁眼处有被撬动的痕迹——是大理寺的人进来时弄的。李承恩让侍卫守在门口,自己则带着左忆往里走。
铺面里堆着各色绸缎,红的像霞,绿的像翡,却都蒙着层灰,显然多日没人打理。穿过铺面往里走,便是周掌柜的卧房,陈设简单:一张木床,一张书桌,角落里堆着几个木箱。
“仵作说,人就是死在这床上的。”李承恩指着木床,床褥已经被收走,只留下块发黑的印记,“血迹都清理过了,但墙角的砖缝里,还能看到点暗红。”
左忆没说话,先蹲下身,对着砖缝仔细看。砖缝里的暗红痕迹边缘有些发乌,她用银探针刮下一点粉末,放进瓷盘里,又倒了点米醋——粉末遇酸,竟泛起淡淡的蓝绿色。
“是砷。”她抬头看向李承恩,声音里带着点笃定,“砒霜中毒,只是剂量不大,所以死得慢,才会咳血。”
李承恩凑近看那瓷盘,见粉末真的变了色,眼底闪过点讶异:“你怎么知道……这么快?”
“砷遇酸会变色,是医书里写的。”左忆没说这是前世的法医常识,只拿起银剪子,走到书桌前。书桌上堆着些碎布,是裁衣剩下的,她用剪子挑出一块深蓝色的绸缎,对着光看,绸缎的边缘有处细微的勾丝,勾丝里缠着点浅灰的绒毛。
“这绒毛不像绸缎上的。”她把绒毛放进透明的瓷瓶里,“倒像是……皮毛上的。”
李承恩忽然想起什么:“周掌柜的邻居说,案发前一晚,见过个穿灰鼠皮袄的人来铺子里,说是来取订做的官服。”
左忆的指尖顿了顿。灰鼠皮……和她身上这件披风的料子很像。
她又去翻角落里的木箱,箱子里装着些旧账册,大多是去年的,记录着绸缎的进出。她一页页地翻,忽然在一本账册的夹层里,发现了张折叠的纸条,上面用炭笔写着个名字:“柳成”。
“柳成?”李承恩凑过来看,眉头瞬间皱起,“是柳太傅的远房侄子,在户部当主事。”
左忆把纸条收好:“柳家倒台后,柳成没被牵连,还在户部待着。周掌柜手里的账册,说不定就记着他的事。”她忽然想起中秋宫宴上扳倒柳家的事,柳家残余的势力,竟还敢在京城里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