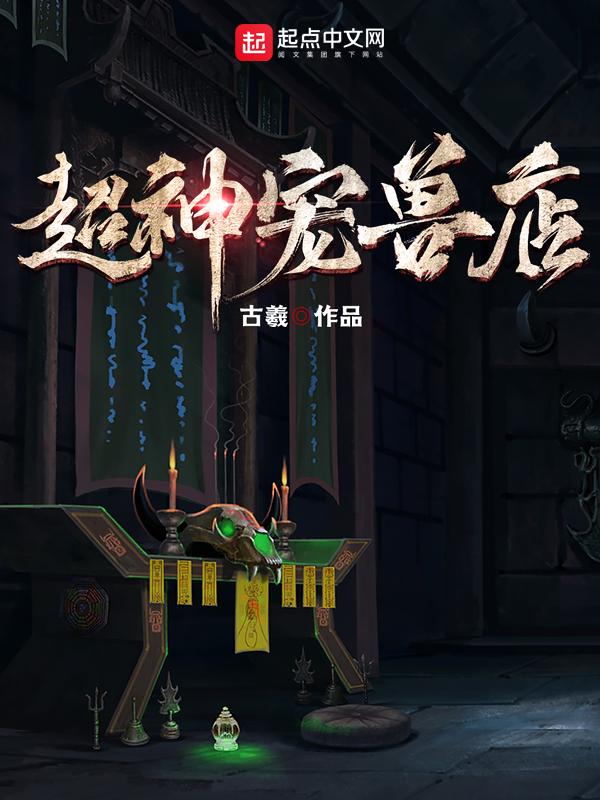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仙君宠兔日常作者流云一叹 > 同船怪客(第1页)
同船怪客(第1页)
就这样,司明镜停止了她的长途跋涉,在这片海边留了下来。
那个教给她“海”这个词语的船工告诉她,这个地方叫“怀州”。
怀州是个大城,一条大河穿城而过,直接入海。为着这个原因,怀州船运发达,城中几个大富商,也都是这一行内的。几百年前怀州城傍河而富,便不满足于内陆的生意,于是几个大商户联合起来,一掷千金,开掘泥沙,兴建护岸堤,在怀州的入海口处强开了港口,以便发展远海的生意。这是一个大工程,好在开始得早,如今这港口早已落成,来往航船不断。
只不过,毕竟是强开的港口,不合地利。商户怕生变故,于是在修建怀州港的同时请了高人指点。那高人大手一挥,要求在靠近入海口处的河道上修一座入海桥。这桥高达百丈、横跨五十余里,修得又高又陡,既无法通人,也无法通车。从河面望上去,最高的一部分桥身隐在云雾里,人在下面甚至看不清桥底。
这入海桥也有几百年的历史,在当地算是一奇观。不过,以现如今的工艺,已经没有人能够建造这样一座高耸入云的巨桥了。入海桥成了怀州可以见到的传奇,当地人传说这桥在建造时得了仙人相助。
司明镜站在甲板上,远远地望向那隐在云雾里的入海桥。
她此刻已经换了一身船员打扮,和丁桑并排站着抽水烟。
这丁桑便是她刚到怀州那日,在海边遇到的船员。说是船员,其实丁桑的工衔要更高一些。
“我是艄工,懂吗?海上的书生,要辨航掌舵的!”
丁桑拉她入船队时是这么介绍自己的。他看起来似乎很骄傲于自己这个工种,还慷慨地允许司明镜在他勘海的时候旁观学习。
就比如,此刻……
“海天不分,妖雾横生……这种时候,就不该出海的。”丁桑看着远处灰蒙蒙海面,眉头紧锁。
司明镜呛了一口烟,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你看看你,怎么还是学不会抽水烟?真是没福。”丁桑舒展了眉头,大笑着给司明镜拍背。
“别拍了,没呛死也要给你拍死了。”司明镜打开他的手。
“那怎么会?”丁桑笑嘻嘻道,“那天十几个人打你一个,都没把你揍趴下,我就看出你体格不一般,是个干苦力的奇才!这么轻轻一拍,算得了什么?”
司明镜脸一冷,“啪”地一下把丁桑嘴里叼着的水烟袋打进了河里。
“哎哎哎!我媳妇好不容易答应给我换的……”丁桑一脸痛心疾首地看着水烟袋飞去的方向,不敢跟司明镜发作,只咬牙切齿道:
“这会儿知道羞了?偷东西的时候怎么不知道?”
“……”
那日司明镜走到海边,已是饥肠辘辘。她这辈子还没有挨过饿,忍到此时已是奇迹。她正头晕眼花,忽然看到一队人扛着一大箱一大箱不知什么东西往岸上走。
鱼。
鱼肉。
司明镜看见了,也闻了出来。她偷偷跟着这些人,到了一个很大的屋子外面——那屋子里全是各种水产、腌肉。
司明镜藏在外面盯了很久,等到屋子里的人都出去后,立刻闪身进去,抓了一条鱼就开始啃。
她接连生啃了三条鱼,如痴如醉,完全没察觉刚刚离开的人已经回来了。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被一棍子抡在背上。颠沛流离一个月,司明镜已经不比从前康健,当时就一口血就喷了出来。
司明镜第一次在打架上吃亏,登时眼睛就红了。转身飞起一脚正中那人胸口将人踹倒,拔了腰间剑,与围过来的其他人相持。她嘴里还叼着碎鱼肉,披头散发,面露凶光,活像地狱里爬出来的小鬼。
可惜,纵然司明镜再能打,也架不住十几个青壮年打她一个。剑被打掉之后,司明镜很快被制服。她满身血污地被按在地上,还在不停挣扎;而按着她的几个人也没讨到好处,个个鼻青脸肿。
……
时隔几个月,丁桑再提起这件事,已是笑谈,可司明镜还是觉得有些不自在。
司明镜抱着胳膊往甲板上一坐:“我当时太饿了。”
丁桑看着她这样子,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行了行了,反正你现在已经是自己人了——水烟的钱从你工钱里扣啊。”
司明镜瞥了他一眼,没反驳。过了一会儿,低着头道:
“我现在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