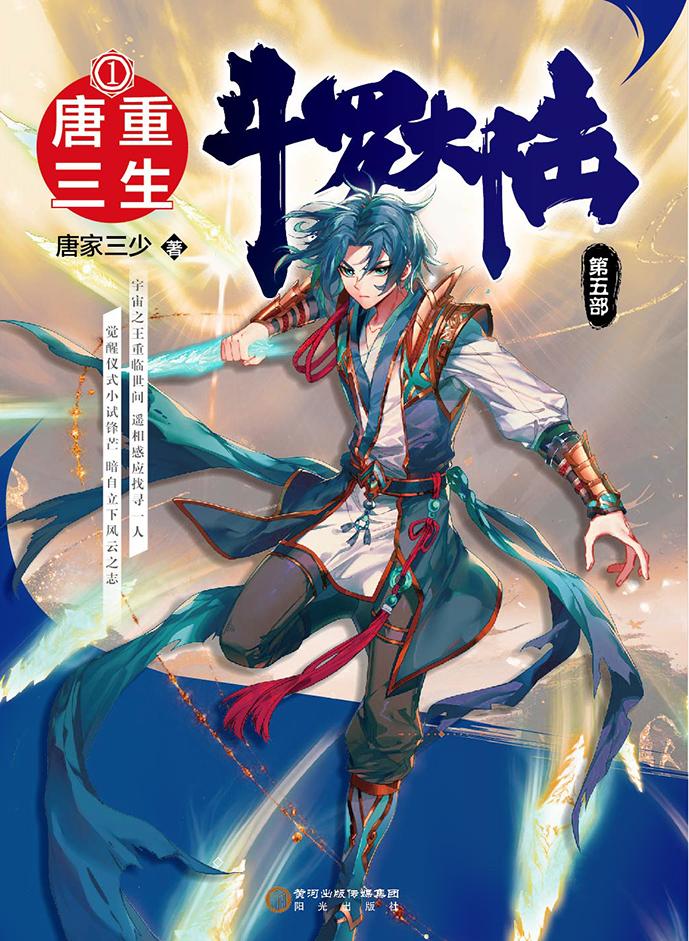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不和师父睡 > 2第 2 章(第4页)
2第 2 章(第4页)
执律堂内,纪楚站在屋子正中央,面色苍白,双腿因跪了一天而有些站不稳,但看不出丝毫惊慌。
“我确实在昨夜出门,但并未去炼器堂,更没有见过袁复。”
执律堂堂主严浩打量着她,语气很凶:
“谁能作证?”
纪楚道:“无人作证,我是一个人出去的。”
严堂主语气带着压迫感:
“荒唐!既无人作证,怎敢自言清白?”
纪楚不解:
“堂主这话说的不对,那旁人一面之词,如何就能证明我杀了人呢?再说了,正因为我无辜被冤,所以堂主才更得查清案件,为我做主。”
她上辈子被沈恪要求静言修心,留给外人的印象多是内向少言、不爱交流,后来越来越多的屎盆子扣在她身上,那一份“内向”却也变成了“阴郁”。
此刻不卑不亢直言相告,反而更容易让人信服。
严堂主面色松动几分,问她:
“既如此,你昨夜去了哪,做了什么?一一说来,我着人去查。”
纪楚闻言却沉默。
严堂主见状,眼神再次充满怀疑:
“你说不出来?”
“不是。”
纪楚否认。
她面色苦恼,解释道:
“我虽没有杀人,去做的事却也不算正大光明,所以才会迟疑。”
说完,她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摸了摸鼻子:
“我去悬鹤峰砸琴了。”
悬鹤峰,砸琴。
这两件事合在一起怎么听怎么不着调。
但纪楚言之凿凿,还伸出两只手给他看:
“沈长老要我练琴,可我实在不喜欢弹琴,怎么都学不会,还弹的满手都是血。一气之下,连夜把琴拖到悬鹤峰砸了。”
严堂主闻言看去,确实看到她十指鲜血淋漓,伤口细长,是琴弦所致。
纪楚又接着说:
“不瞒堂主,我之所以这般走路都走不稳的样子,就是因为砸琴惹怒了沈长老,这才被罚跪了一天。”
严堂主听闻后,不禁在心里叹道:
沈长老平日看着温润如玉、进退有度,谁想私下教导弟子时,竟是这么个偏激性子。
音律一道先谈自娱,而后才谈苦修。纪楚到底不是他的弟子,何苦非逼着人学琴,还学到这般地步呢?
他心下已经偏向了纪楚,但仍按照规矩道:
“这些都只是你一面之词,具体真相如何,我尚需派人调查……”
他还没说完,便见一个弟子匆匆跑来,附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
严堂主登时睁大双眼,看着十分震惊,连让纪楚“先回去”都来不及说,急忙跟着那个弟子从另一扇门出去了。
甚至他出门前还专门整理了一下衣摆,像是要去见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
留下纪楚原地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