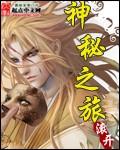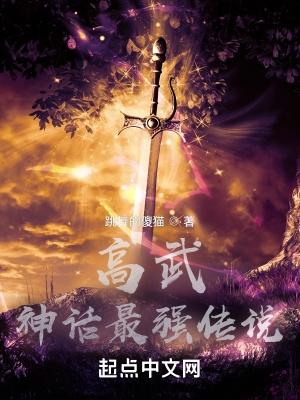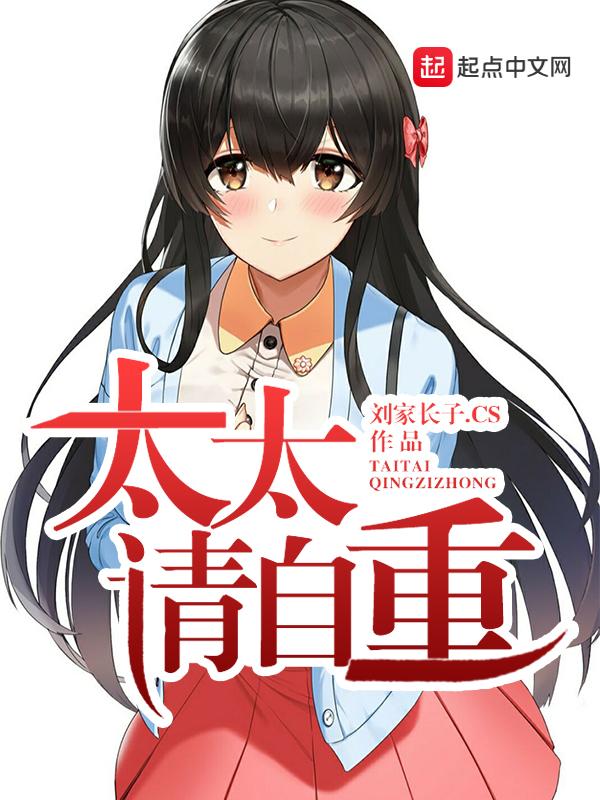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以下犯上怎么解释 > 司灵一(第2页)
司灵一(第2页)
倒是另一人诧异地看了那冷脸救星一眼,随即上前几步,将那老者搀了起来。
“既是老人家,去旁边歇一歇罢。”谢攸嗓音温和。
他原想着,这忌虚白既然是晋王的老师,那他此时应当只需摆出一副“隐居仙人”的姿态,其他事自有人料理。
于是扶起老者,正欲凛然有度地一坐,谁料李焉隅把过脉后,竟扯了扯他的袍袖,示意他近前细看。
谢攸暗道不妙。先前在茶馆的应对实是歪打正着,此等侥天之幸,难不成还指望能再撞上第二次?
他抬眼看向李焉隅,对方指尖仍落在袖口,没有半分松开的意思。
谢攸默了默,心下一横:左右有这个晋王在,便是出了差错,总也有个兜底的。
如此想着,便也蹲下身,双手同时搭上腕脉。
那脉息无力至极,轻飘得像一缕烟,忽明忽灭的。稍一用力按下去,竟如同探不到底般,空空荡荡。
就好似悬崖边的绳索,一端系着将坠的人,另一端却在一点点磨断。
谢攸眉峰微蹙,又挽起容斟和的袖子一摸,皮肤厥冷无边。
他略一沉吟,道:
“得用些峻补元气的药,先固住根本。”
李焉隅正将那医者扎错位置的针一根根拔出来。银针离开皮肉时,带出一点极细的血珠,很快便被容斟和身上的冷汗冲淡了。闻言道:
“我也是这个意思。只是容指挥使他……不大受补。”
他还在琢磨该怎么在众目睽睽之下同谢攸讲清此事来由,旁边有嘴快的玄镇卫先开口了。
原来早年间,容斟和大病初愈时,满朝文武为了讨好这位圣上眼前的红人,各式各样的参汤补药流水似的往府里送。
谁知他喝了一碗参汤,那病竟似去而复返,突然发起经久不退的高烧。太医一瞧,只道“虚不受补”,又仔细调养了好几月,方见起色。
自那以后,再没人敢让这位指挥使沾半点补药。
谢攸的指尖仍搭在容斟和的腕上,听罢沉默了片刻。堂内的灯在他脸上投下极淡的光影,倘若凑近细观,便能看见他睫毛轻颤,像是在盘算着什么。
片刻后,他复又开口。
“不行,此危非大补之药不能解。去取净萸肉四两,越快越好。”
李焉隅闻言,对着何云争吩咐了几句。何云争迟疑一瞬,最终还是领命而去,玄色的身影消失在了雨幕中。
不过半炷香功夫,他便去而复返,身上的飞鱼服已经湿得不能再湿,在地上拖出一路的水痕。怀里的药包倒是裹得严实,半点也没淋着。
满堂除了李谢二人,便只剩下半吊子医官和一帮屏息静气的玄镇卫。谢攸环顾四周,正欲去煎药,李焉隅却轻轻按了按他的手腕,自己起身接过了药包。
炉里烧得是暴火,不多时,便有水汽从罐口里冒出来。萸肉倒进去的瞬间,屋子里弥漫起一股酸涩的药味,带着草木的清苦气,倒也不算难闻。
药沸过整遭,李焉隅叫人盛出些许。他先在容斟和门穴上叩击数下,指腹又碾过手腕内侧的关穴,末了取银针缓缓刺入,针尖几乎不见晃动。
他的动作很沉,指节紧绷,眉眼垂落时,带着一种近乎肃穆的庄重,仿佛在进行某种仪式。
堂内有玄镇卫瞧见这一幕,忍不住窃窃私语:原来这便是司灵了。
待到药汁煎得极为浓稠,这才用小巧的银勺,一点点将药灌了下去。
不过片刻,容斟和额间的冷汗便收了些,骇人的面色也稍有缓和。
李焉隅又唤人添了水,再煎药渣,直到滚了数沸,才又喂他饮下。如此反复,待到第三碗药煎好灌下,伸手一探,四肢的厥冷已经缓了过来,也能自主地喘匀气息了。
堂里众人这才齐齐的松了口气。李焉隅没理会玄镇司上下,只转向何云争,低声嘱咐了几句。
何云争躬身如仪,连声称“是”,又行了个大礼,就要送李谢二人出门。
“等等。”
一旁默不作声的谢攸却冷不丁开了口。他蹙着眉,手里捏着一纸掉出来的案卷——何云争走得匆忙,只来得及收拾了桌子上的,却没留意指挥使大人身上还揣了一张。
他原没打算多管。玄镇司的案子,本也与他无关。正想悄无声息地塞回去,可纸上“书院案”三字,偏就这样撞进了他的眼里。
“你们今夜审的是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