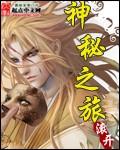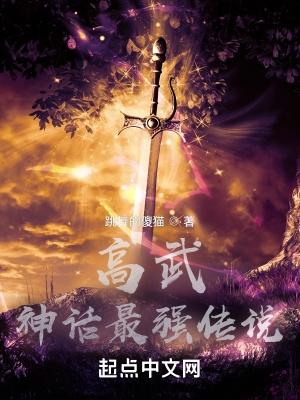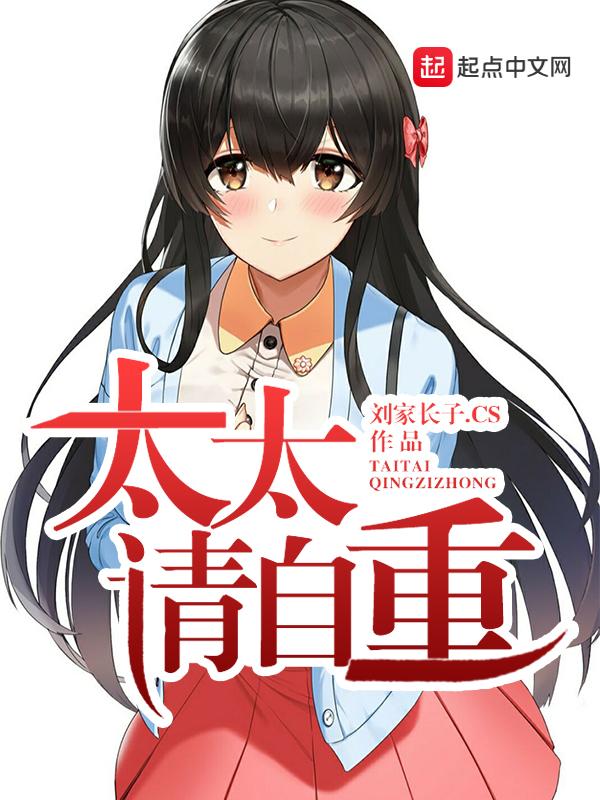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黄滕酒描写谁的爱情 > 新岁余寒(第1页)
新岁余寒(第1页)
庚午年正月初五,年节的余韵尚浓。永州城里,庙会市集正是最热闹的辰光。
长街之上,车马辚辚,人流如织,直似沸水开了锅。各色百货物件琳琅满目,奇巧玩意儿引得孩童嬉笑追逐,小贩们高一声低一声的吆喝此起彼伏,更有那戏班子锣鼓喧天,围观的看客喝彩声震得檐上积雪簌簌落下。
沿街的酒楼戏馆、高门大户,依旧悬着簇新的红灯笼,贴着鲜亮的门神春联,一派富贵太平景象。
然而,这市井的喧嚣鼎沸,行至城郊玉清观的山门前时,便倏地沉寂下去。一条青石小径蜿蜒入林,幽深静谧,只闻松涛低语间或有几声清越鸟鸣。
前来进香的善信三三两两,稀稀落落,衬得这处清修之地愈发冷寂。一辆四角悬着“唐”字灯笼的青帷锦幔马车停驻在略显空荡的观前,便显得有些突兀了。
车帘掀开,唐府的老夫人怀里紧抱着刚满月的小孙女唐醒,被仆妇搀扶着步下踏凳。观中一位眼尖的小尼姑早已认出,忙不迭地迎上前来,双手合十,口称“老夫人万安”。
唐府乃永州数一数二的富户,这位唐老太太的来历更是显赫,她是雍州首富的嫡长女,当年嫁给唐家那位著作郎时,那十里红妆的盛景,从永州城东一路绵延到城西,至今仍是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谈资。唐家由此跻身巨富,老太太又素来乐善好施,在这永州地界,认得她这张慈和面孔的人,委实不少。
老夫人面上带着一贯的温和笑意,微微颔首。小尼姑恭敬地引着老夫人一行人,穿过几重肃穆的殿宇,直往观内更深处的后院行去。
这行人的背影刚消失在月洞门内,观前石阶下几个歇脚的香客便低声议论起来。
“咦,那不是唐府的老封君么?瞧着气色似乎不太好。”路人甲压着嗓子道。
路人乙立刻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快莫高声!他家府上近来可不太平。他家那位大娘子,去年腊月根儿上……没了!”
路人丙闻言一惊:“啊?不是说是难产伤了身子,一直缠绵病榻么?”
路人乙摇摇头,声音压得更低,带着几分神秘:“外头是这般说。可我听在唐府做浆洗的远房亲戚提过一嘴,说大娘子去得急,是生生被气吐了血……这件事唐老夫人脱不了干系!”
路人甲显然不信,声音不由得拔高了些:“怎么会!老夫人素来是出了名的仁慈宽厚,待人接物最是和善不过,怎会对自家媳妇……”
话音未落,唐老夫人身边那位面容严肃、眼神锐利的孙妈妈已走了过来,目光迅速扫过三人,沉声道:“菩萨跟前,口德最是要紧。无端妄议,仔细报应不爽!”
三人被这气势所慑,又见孙妈妈衣着体面,显然是唐府有头脸的管事妈妈,当下噤若寒蝉,讪讪地互相拉扯着,快步散开了。
后院禅房外,一株老梅疏影横斜,暗香浮动。无念师太正于蒲团上闭目打坐,气息悠长。老夫人抱着襁褓,示意随行人等噤声,只带着孙妈妈和抱着孩子的奶妈子,静静侍立在一旁等候。
奶妈子怀里的婴孩睡得正沉。许是脚下踩着了一块尖石子,奶妈子身形一晃,手下意识地一紧。那襁褓中的小人儿受了惊扰,小嘴一瘪,“哇”地一声啼哭起来,声音虽弱,在这寂静的院落里却格外清晰。
无念师太缓缓睁开眼,眸光清冷如水,掠过老夫人一行人,最终落在啼哭的婴孩身上,面上无悲无喜,只淡淡道:“老夫人移驾至此,所为何事?”
老夫人上前一步,忧心忡忡道:“此处人多眼杂,可否请师太移步内室一叙?”
无念师太瞥了她一眼,起身拂了拂素色道袍,径自转身推开了禅房的木门。老夫人连忙跟上,从奶妈子手中接过孩子,示意孙妈妈带人退至院中,并亲手将房门掩上。
室内檀香袅袅,陈设简朴。老夫人抱着啼哭渐止、只余抽噎的婴孩,开门见山道:“不瞒师太,我这苦命的孙女儿,自打出生便体弱,近日更是高烧不退,延请了数位名医,汤药不知灌了多少,却如石沉大海,不见半分起色。前日请了位道长来看,说是……冲撞了什么不干净的,受了惊吓,指点我务必带着孩子来玉清观寻师太您,唯您有化解之法。”她语速急促,眼中是满是焦灼与期盼。
无念师太走近,伸出枯瘦洁净的手指,轻轻掀开婴孩的襁褓一角,露出孩子烧得通红的小脸。
她凝神细看片刻,眉头微微地蹙了一下,随即收回手,缓缓走到一旁的红木禅椅上坐下。她闭了闭眼,复又睁开,语气平淡却且笃定:“逝去亲人缠身,此非药石可医。此乃尔等昔日种下的恶因,如今这稚子,便是你们不得不咽下的苦果。”
老夫人心头一紧,将孩子抱得更牢:“师太!此言何意?莫非……没有别的法子了?”她声音颤抖。
“将她送出去养吧,最好是把这孩子送去她母亲的娘家,那里是孩子的福地,也能让逝去的亲人放心,”无念师太的声音毫无波澜,“否则,此女……断然活不过三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