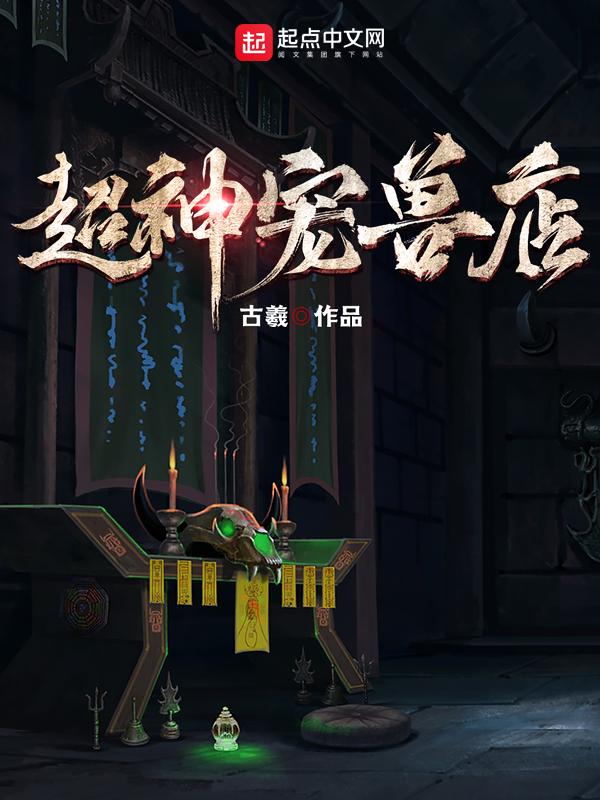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黄滕酒描写谁的爱情 > 骨肉远送(第1页)
骨肉远送(第1页)
卯时的更锣刚敲过不久,晨曦的微光勉强刺破冬日的薄寒。
唐老太太已起身,径直去了昆哥儿和醒姐儿同住的“兰馨堂”。
屋内炭火尚温,暖意裹着安眠的气息,两个小人儿犹在酣睡。奶妈子和那个才五六岁光景、名唤彩云的小丫头早已收拾妥当,奶妈子正欲去抱暖炕上襁褓中的唐醒,见老太太裹着一身寒气进来,忙躬身敛衽退至一旁,彩云也垂手侍立,屏息凝神。
“孙妈妈交代的话,可都记牢了?”老太太的声音不高,带着一夜未眠的疲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紧绷。
“回老太太,都记下了。”奶妈子低声应道,声音里透着小心。彩云也用力点点头,小脸绷得紧紧的,一双眼睛却格外清亮。
老太太缓步走到暖炕边,俯身凝视着熟睡的孙女。小人儿烧已退了不少,小脸却依旧苍白得惹人心疼。
她伸手替她掖了掖被角,指尖忽地触到被窝里一个坚硬的小物件。她轻轻拨开被角,只见唐醒肉乎乎的小手边,静静躺着一个精巧的银铃铛,红绳系着,小巧玲珑。
“这是……”老太太眉头微蹙,指尖捻起那冰凉的小铃。
奶妈子连忙解释:“是昆少爷。他……似是知道醒姐儿要离府,昨儿夜里巴巴地让木头送过来的。少爷说……有了这铃铛声响,无论醒姐儿去哪,他都能循着声儿找回来。”
老太太指尖摩挲着冰凉的银铃,沉默片刻,眼中掠过一丝复杂难辨的情绪,最终归于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昆哥儿是个重情的……也罢,就留着给醒姐儿当个念想吧。”她将铃铛轻轻塞回孙女掌心,掖好被角。
卯时一刻,唐英亲自抱着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张小脸的唐醒,登上了驶往城东李府的青帷马车。
车轮碾过清冷寂寥的街道,发出单调的辘辘声,仿佛碾在唐英的心上。天光渐亮,街市上行人渐多,车马喧嚣起来,衬得车内愈发沉闷。
当唐府的马车最终停在李府那朱漆兽环、气派森严的大门前时,唐英的心也沉到了冰窖里。自李氏亡故,他便再未踏足此地,今日此行,无异于闯那龙潭虎穴。
李府门房的护院远远瞧见车驾上悬挂的“唐”字灯笼,脸色便是一凛。一人飞也似的奔向内宅通传,声音都变了调:“老太太!老爷!太太!唐……唐府来人了!”
李府的李玉官拜永州曹侍郎,其母宋氏乃一等永毅伯府的嫡次女。唐府大娘子李如月是李老太太的嫡女,一言一行落落大方,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对母亲更是知冷知热,是老太太的掌中宝。
当年为求娶李如月,踏破李府门槛的高官子弟不知凡几。至今提起李如月,李老太太仍是痛心疾首,恨其识人不淑。
唐英被引着穿过熟悉的庭院回廊,步履沉重如灌铅,每一步都像踩在荆棘之上。及至“如意堂”,一股无形的压力扑面而来。
只见李老太太端坐于上首金丝楠木的玫瑰椅中,面沉如水,手中佛珠捻得飞快。长子李玉及妻曹氏分坐两侧,三人目光如炬,森冷如冰,早已等候多时。
堂内檀香袅袅,气氛却凝滞得如同结了冰。
唐英一脚刚踏进门槛,便被那三双利剑般的目光钉在原地,脊背瞬间爬满寒意。他硬着头皮上前,深深一揖,声音干涩紧绷:“小婿唐英,拜见岳母大人,舅兄,舅嫂。”
李老太太眼皮子都未抬,只从齿缝里冷冷挤出几个字,字字如冰锥:“你还有脸登我李家的门?”
唐英被这劈头一句斥得面皮紫涨,手足无措地站着,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小婿……自知有负如月,今日厚颜前来,实是有事相求……”
“相求?”李玉猛地一拍扶手,怒极反笑,声音震得梁上微尘簌簌,“求什么?求我们放过那个气死我妹妹的贱妾徐四?还是求我们替你姨母徐家那摊子烂事疏通关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