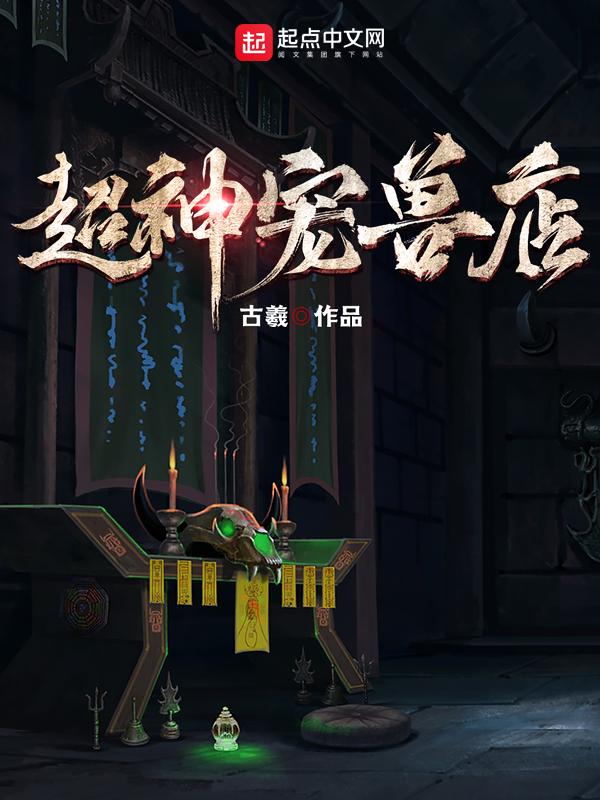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农夫悍妻种田忙 > 省得心累(第2页)
省得心累(第2页)
已至暮时,远山云霞漫天,倦鸟成群归林,一片寥落闹景。
裴松伸个懒腰站起身,跨门出去,院子里裴榕正在收码柴火,他归家时见大哥睡着,便自顾自将柴火劈砍了。
“啥时候回来的?”裴松走上前,将柴火往柴房里搬。
裴榕力气大,抱起一大摞跟上裴松的步子:“也才回来。”
哥俩儿一前一后进了屋,裴家房舍虽破旧,收拾得却干净,柴火挨墙堆码齐整,另端的角落里是个半人来高的新竹筐,里头放着农耕用具。
夏时天气多变,前几日大雨倾盆,将屋顶打漏个角,好在破口不大,雨水没浸到柴火,要么有的忙了。
裴榕将柴火堆好:“等明儿个空下,我上房将屋顶修了。”
上房得爬梯,家里没这用具,需得去邻家借一把,因此补屋的事宜一拖再拖。
可马上入炎夏,到时必得暴雨,屋顶不补只会越漏越大。
“成啊。”裴松掸了下灰,“那明儿个我早些回,给你打下手。”
兄弟俩亲近,说话自是无需避讳,拾掇好了柴堆,裴榕将门栓好,缓声道:“阿哥,你俩成亲,要请那家人吗?”
那家……秦家。
裴松皱紧眉,依他二弟寡淡的性子,若不是听到什么,断不会多这句嘴,他干脆问道:“你这是听到啥了?”
裴榕沉默片刻,照实了说:“其实小半月前就有婶子随嘴问过,我没当回事,谁承想这几日竟传开来了。”
“传开来了?”裴松不自觉握紧拳头,“咋个传开法?”
裴松做工的地界在村口闹街,虽在尾头的犄角旮旯里,可多经营红白喜事生意,来往颇多。
前儿个近村的王猎户家嫁女,王家婶子过来打妆奁匣子,闲聊间提及了秦既白。
因着两家同为猎户,相识多年有些交情,侄儿又与秦家大郎岁数相宜,王家本意牵线搭桥将小侄嫁过去。
谁料打听后知晓,秦铁牛那继室着实不是省油的灯,将秦既白搓磨得不成人样。
“我瞧着都不落忍,可非亲非故的说话不作数,人家不承情不说还要嫌我啰嗦。”王婶子直摇头,“好在没将笋哥儿嫁过去,要么日子过得一团糟,我两边不是人。”
裴榕没接话,只将妆奁匣子的样货往出拿,可那婶子打开了话头,嘴里不歇:“后又听闻那秦家大郎寻摸上亲事了,说是个裴姓老哥儿,哎呦这哥儿可非善茬,该是长久嫁不得人心里出了毛病,如那黄风妖般生逼着人娶!”
她拍把手,口中啧道:“秦卫氏虽薄待继子,可秦铁牛却生养有恩,成亲了连亲长也不叫请,你说这叫什么事?!”
裴榕冷淡瞥了一眼:“婶子话里偏颇,裴家从没强逼过人。”
“你又咋知道哦?”
“您方才说的那位裴家老哥儿,是我亲哥。”
……
裴松一手杵墙,弯下腰嘎嘎直笑:“可给那王家婶子吓一跳吧,背后嚼舌根嚼到苦主跟前了。”
裴榕面无表情地点点头,心说也就是他大哥,心眼麦秆似的粗,被人这般编排还咧大嘴乐,他抿了下唇,缓声道:“那到时候成亲,还请秦家吗?”
“不请。”裴松正了正色,抱臂道,“他家作恶却反打一耙,我瞧见都恶心,若非怕白小子夹在中间难做,卫氏又才失了孩子,真想打进他家门讨个说法。”
立夏前后落大雨,偏就这般寸,卫氏在自家院子里跌了一跤,躺了两日不见好,小月的娃儿就这般没了。
这事还是裴松去陈郎中那拿药,听来看诊的婆子说的,他是厌烦卫氏,却也能体谅。
裴榕不置可否,只道:“可与秦既白知会过了?那毕竟是他亲长。如若不提,恐生嫌隙。”
裴松拍了拍裴榕厚实的肩膀:“是长大了,知道操心哥的事儿了?”
裴榕好脾气地笑:“那我不管了,省得心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