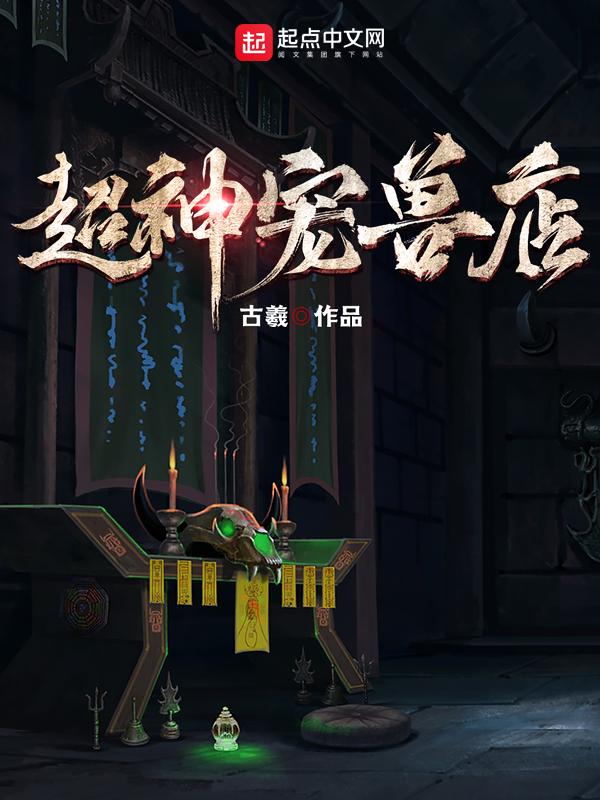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农门悍妇宠夫忙 > 一人一半(第2页)
一人一半(第2页)
裴松将铜板放到桌面上,可脚下却没动,他踌躇了片刻:“大肉的几文?”
“大肉面四文。”
裴松咬了咬牙,又垂头捻出几个铜板:“一碗里加个大肉吧。”
日头高升,人流逐渐多了起来。
秦既白坐在矮桌前,百无聊赖地看着熙攘的街巷。
待到裴松回来时,他手里多了个油纸包。
刚出锅的烧饼,表面撒了一层黑芝麻,又酥又脆,那味道香得人涎水直流。
裴松才屈膝坐到凳子上,店伙计也端着面条上了桌,他笑着看向裴松,见人抬下颌点了点对面,便心领神会的将有肉的那碗面放到了秦既白跟前。
秦既白看了看自己这碗,又看了看裴松那碗,伸筷子将大肉块儿夹到了裴松碗里。
“哎哎这是干啥呀?”裴松正在撕饼子,这热腾劲儿就是隔着油纸都还烫手,他龇牙咧嘴地甩了甩,却被秦既白一把抓住腕子,捧到嘴边轻吹了起来。
男狐狸,不怪裴椿说他,秦既白长得是好看,都不能只单说好看,是整个村子里数一数二的俊,一张白面庞咋晒都不发黑,一脸病气却不显得萎顿。
裴松愣了会儿神,忙又将手抽了回来,笑得颇有些局促:“不烫了。”
秦既白“嗯”一声,无事发生般拿起筷子搅了搅面,见裴松没动,又端过他那碗,帮着将面搅散开。
一碗素面一碗肉面,加了大肉的那碗,底汤是用猪油炒香的,上面飘了一层细密的油花,秦既白眼尖,不动声色地换到了裴松跟前。
裴松正把饼子掰开,自己留了小的那边,将一多半递了过去:“哥饭量小,肉给你吃。”
他正要将肉块夹回对面碗里,秦既白伸手将碗遮住了,挺瘦一个人,手却大,能将面碗遮个七七八八:“那一人一半,好不好?”
汉子平日里便沉静,眼下开了口也是温温和和的,可裴松偏从那询问声里听出了苞米碴子似的黏黏糊糊,和少时他哄裴椿似的,腻歪、娇宠,听得人耳根子发烫。
秦既白见他不答话,接了那半只饼:“这饼子就是我多,那肉你的多些。”
“哥真的不饿。”
秦既白抬头看了他一眼,两手并用将肉块儿自中间截断,稍大的那块儿放到了裴松的碗里:“快尝尝。”
裴松皱着眉头还想推拒,秦既白已然挑了一筷子面进嘴里,见人迟迟不动筷,他轻声道:“人都看着呢。”
裴松转过脸,这才瞧见邻桌的大娘正笑眼吟吟地看着他俩,见他也看过来:“你这夫郎真是好,啥都紧着你来。”
裴松稍愣,本以为这大娘是在同秦既白说话,可那红润饱满的脸又分明正对着自己,他有点儿赧,哑然失笑:“大娘,他、他不是我夫郎。”
秦既白抬起头,缓声道:“我是他相公,眼下还不是,快成亲了。”
“哎哟!”大娘愣了愣,目光自俩人脸上来回游移,可不咋的,正对脸的才是哥儿,虽然身板子壮实,长相也普通,可那眉宇间不正有颗小痣。
哥儿的眉心才长孕痣,越是红润越是好生养,他这颗虽然才针尖儿大小,又暗淡无光,可确是哥儿才有的痣。
“瞧我这眼神,年纪大了不中用了!”大娘一个劲儿地埋怨自己,倒是裴松笑着帮她解围,又直言自己这模样确实不咋像哥儿,不怪她看错。
这种事儿他遇见得多了,早已经不觉得有啥,他把自己锻炼得心宽少思,要么锱铢必较闹起心来,日子没法过。
面条是现抻的,嚼在嘴里很是筋道,确实比家里刀切得好吃。
裴松吃了两口就觉出汤味道不对了,他头回来这铺子吃面,只以为大肉面是素面上头盖一张厚实的肉块儿,却不想连汤里也这么多门道,他咬了口烧饼:“我说你干啥将这碗换给我。”
秦既白抬起头沉静地看他,也低头咬了口烧饼,芝麻的香味在唇齿间弥散,他轻声道:“没人规定哥儿该长啥模样。”
这话前言不搭后语,可裴松知道他是在回他方才替人解围的话,笑着喝了口面汤,脸上泛起红:“臭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