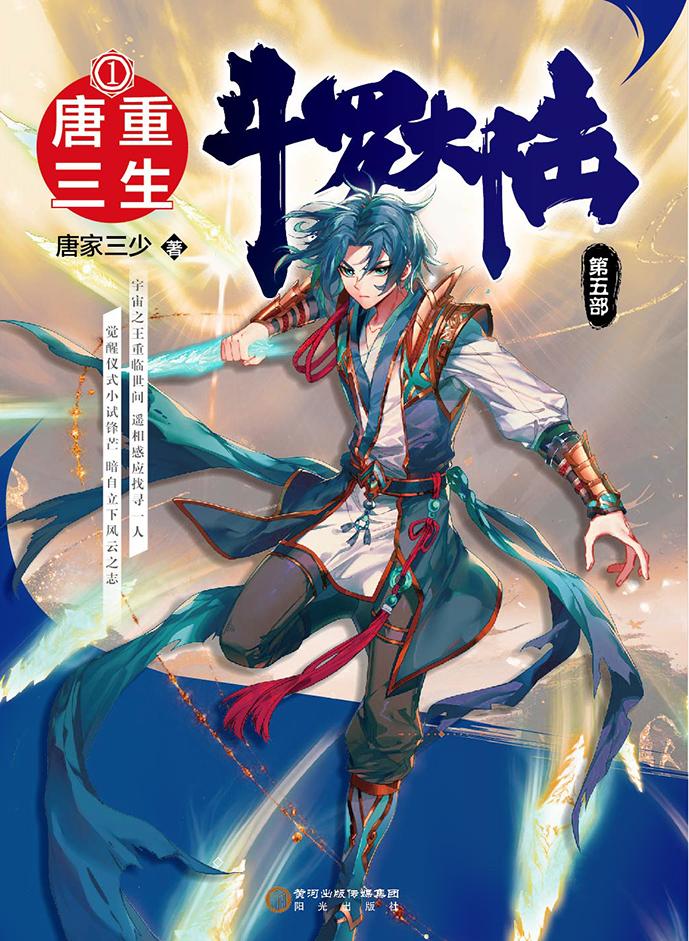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南过猿声一逐臣 > 潜鳞(第2页)
潜鳞(第2页)
郑阎立刻转身,眼中重新燃起希望:“相爷还有什么吩咐?”
裴霄雪抚着案上青瓷笔洗,那是他的亡妻郑芊芊生前最爱用的物件,釉面养得如脂如玉:“妻贤夫祸少。”他抬眸,眼尾笑纹如刀刻,“您说是不是?”
郑阎愣了片刻,突然红光满面:“相爷说得对!芊芊表妹在天之灵……”
裴霄雪不置可否地笑了笑,重新拿起公文批阅。待郑阎退下后,他取出一方雪白丝帕,慢条斯理地擦拭着方才被郑阎碰过的桌角。
窗外的风吹动帘幕,一树晚樱正落得凄艳。
时琛走出宫门时,天色已近黄昏。朱红的宫墙在落日余晖下泛着血色,他站在高阶上,袖中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礼单的残角——那是方才呈给皇帝的赔罪礼单,如今只剩他手里这一小片。
宫道上的风卷着轻微的凉意扑面而来,吹散了他面上维持得体的笑意。
半个时辰前,紫宸殿内。
时琛跪在光可鉴人的金砖上,背脊挺得笔直,绯红世子礼服衬得他面容如玉。
“臣管教不严,致使御赐之物损毁,特来向陛下请罪。”他声音清朗,双手奉上礼单,“崔氏家贫,其母难以视物,幼弟病弱,臣一时心软,改鞭刑为罚役,实属僭越。”
萧景琰倚在龙椅上,指尖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扶手。礼单被太监接过,却连看都没看就搁在了一旁。
“哦?”皇帝轻笑,“朕记得那瓶子,是先帝赏给你祖父的。”
殿内陡然一静。
时琛额角渗出细汗,却依旧保持着完美的仪态:“正因是先帝遗泽,臣更不敢令其沾染人命。崔氏女虽为奴籍,然孝心可鉴……”
他编得冠冕堂皇,从《礼记》扯到《孟子》,甚至搬出“仁政”之说。说到后来,连他自己都觉得荒谬——为了给一个奴隶求情,他竟在御前夸夸其谈仁义道德。
萧景琰忽然笑了。
“永宁侯教子有方啊。”皇帝抚掌赞叹,目光却幽深难测,“世子年纪轻轻便知体恤下情,实乃侯府之幸。”
那“幸”字咬得极重,像一根针扎进时琛耳中。
“臣惭愧。”时琛伏地叩首,借动作掩去眼底的异色。
宫门外,时琛深吸一口气,将礼单残角碾碎在掌心。
萧景琰最后那句话在他脑中回荡——“侯府之幸”。究竟是夸赞,还是警告?
他忽然想起父亲今晨的厉色叮嘱:“记住,在陛下面前,你只是个不懂事的世家子。”
天色渐沉,时琛整了整衣冠,抬步走向候在宫门外的马车。车帘落下时,他绷直的肩背终于松懈下来,露出一个自嘲的笑。
暮色漫过宫墙,皇宫另一边的夹道已浸在阴翳里。
一个瘦削的太监贴着墙根疾行,脚步轻得几乎无声。他抄了一条鲜少有人走的小路,穿过几道半朽的侧门,绕过打盹的侍卫——那侍卫听见动静,懒懒地抬了抬眼皮,与他目光一对,又若无其事地垂下头去。
太监没停步,七拐八绕,终于到了一处荒僻的院落。寒芜苑的匾额早已斑驳,漆皮剥落,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寒”字,在风中摇摇欲坠。
院子里,萧咎正坐在石阶上擦拭一把小刀。刀刃薄如蝉翼,映着最后一缕天光,在他指间翻出冷冽的弧度。听见脚步声,他头也不抬,只淡淡道:“公公来了。”
太监快步上前,恭敬地行了一礼:“八殿下。”
萧咎抬眼。他脸色苍白,身形瘦削,眉眼间隐约透着几分锐利,仿若未开刃的刀。少年人的年纪却不见一点朝气,一双狭长眼静得可怕,像是结了冰的深潭,半点情绪都透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