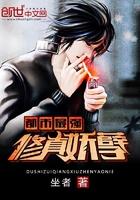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风沙过敏图片 > 第 9 章(第2页)
第 9 章(第2页)
终究还是来了。
躲不开,推不掉。
他看着那刺眼的“客户指定”,胃里刚吃下去的饭菜似乎又开始隐隐翻腾。
昨天办公室里的专业讨论,餐馆里微妙的气氛,顾砚深沉的注视,那句“念想”,还有那个令人窒息的噩梦……瞬间又涌了上来。
他闭了闭眼,再睁开时,眼底只剩下疲惫的认命和一层冰封般的职业冷静。
指尖在键盘上敲击,回复简短而公式化:
萧然:1。
发送。
萧然:对了,昨天忘记说的一点,顾老师这个案子需要进行生物保藏,问一下有没有做保藏,如果没做,尽快去,需要把保藏证明的电子版发过来。
沈锐:好的,我去问,谢萧哥提醒。
他关掉沈锐的对话框,仿佛也关掉了关于顾砚的所有杂念。
流程系统很快推送了案件撰稿过来,发明名称:芽孢杆菌N7及其应用,撰稿人:萧然,返稿期限12个工作日。
时间不算紧迫,足够他处理手头更紧急的审查意见。他深吸一口气,将顾砚的案子暂时压到了待办事项的“下层”。
萧然决定让自己先处理更紧急、更“安全”的工作。
“萧老师!救火!”韩骁一脸焦急,“武汉和上海那两个客户,上次电话沟通了专利布局思路,他们还是觉得心里没底,非要当面聊聊!一个搞化学成分制药的,一个做中药组合物的,都挺重要。主要是教他们怎么整理交底书,讲讲审查流程,再现场帮他们初步检索一下,给新创性把把关。你看……下周能抽四天出来吗?武汉一天,上海一天,路上估计得两天,速战速决!”
萧然看了眼日程,又瞥了眼目前几个待撰写案子的返稿期限,周末加加班,即使扣除四天出差,时间也够。
“行,行程发我。”萧然答应得干脆。
奔波的日子接踵而至。
武汉的客户是家初创药企,年轻的创始人带着团队,对专利既渴望又懵懂。
萧然花了整整一下午,从技术交底书的结构讲到权利要求书的撰写逻辑,再结合他们研发的抗癌新分子,现场检索现有技术,分析新颖性和创造性风险。
对方听得全神贯注,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
紧接着飞上海。
客户是一家老牌中药企业,研发总监是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对组分配比和效果数据如数家珍,但对专利法条却一知半解。
萧然重点讲解了中药组合物创造性判断的特殊性,尤其是“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的判断标准,并结合他们一个治疗失眠的组合物,分析了现有技术组合的可能性。
老师频频点头,直呼“受益匪浅”,直言“专业的事情就该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奔波在机场、高铁、客户会议室之间,萧然像一个高速运转的精密仪器,大脑被各种技术名词和法条塞满,身体疲惫,精神却因这种远离A市和顾砚的“真空”状态而获得了些许喘息。
他甚至刻意忽略了手机里来自沈锐的、关于顾砚项目的零星进展汇报。
然而,就在他从上海虹桥机场登机,准备飞回A市的前夕,沈锐的电话还是追了过来。
“萧老师!顾老师那边开始整理第二份交底书了!是关于一个基因的技术,听起来挺高端的!具体怎么样我也听不懂,他好像有点拿不准,想跟你先沟通下思路!”沈锐的声音在嘈杂的机场背景音里不甚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