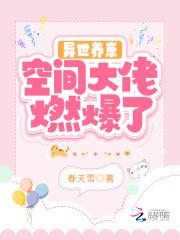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簪缨世族by缓归矣TXT > 第39章(第2页)
第39章(第2页)
崔述一愣,接过仔细翻看,摇头道:“用的是官定的靛蓝染线,装订针法与孔距也不见不妥,各页纸墨成色皆无异,页中有钤印,字迹亦无模仿作假之迹,一应事宜并无造假之迹,我倒并未看出来这册子有问题。”
“文书作伪历来是涉官案件的重点侦查方向,薛向也定派人将这册子翻来覆去查了数十遍了,想来并无所获。你认为有何不妥之处?”
听他如此说,周缨这会子却有些不太确定了,只道:“刑部能人众多,若刑部认为没有蹊跷,想必是我想错了。”
“未必。”崔述引她继续往下说,“你未曾习过断案章法,虽可能剑走偏锋,但也因此不落窠臼,更能别具巧思,恰是断案关键也说不定。”
受他鼓励,周缨思虑片刻,肯定道:“按《则例》规定,官府公文簿册皆用靛蓝染线不假,后廷亦同此制,但据我近来接触之文书,官用线材乃京郊产的净蚕线,这册子用的却是宁州的明丝线,两者粗看质地极其接近,若非常事蚕桑者,分辨起来极有难度。”
在心中再度斟酌片刻,周缨极肯定地接道:“但净蚕线质地微糙,公文翻阅频繁,为避免散册,常例用的是六股。明丝线则更韧,市面常售的较净蚕线少一股,也能达到相似效果。总之,即便纸墨字迹钤印皆无错漏,这亦不是发运司给押纲官的那本册子。”
她鼓足勇气,说出自己的猜测:“要么这一开始便是本伪册,要么有手艺精巧的工匠于后拆解,并按原有印迹重新装订过,故看来与真册并无差别。”
崔述将册子翻至一月廿四沉船那日,仔细再阅了一遍当日的记注,“船行至真定县,突遇急雨,水涨两尺三寸,行船沉没九艘,余七十九艘”。
仍旧没有破绽,漕河定例,一船载四百石粮,确沉没三千六百石粮。
然而若周缨所言非虚,这漕运日志下当有蹊跷。
崔述慢慢将那册子攥紧了:“我会将此言转告薛侍郎,若此案告破,首功当是你。”
周缨一笑:“我还不敢论政,是要论功,还是要砍我头还难说吧?”
那笑比案上的娇杏更显春日暄妍,崔述不禁跟着笑了下:“在景和宫做事如何?”
他毫无芥蒂地问来,似乎如方才所言,当真已将易哥儿之事彻底放下,再无半点介怀。
她一时有些懵,间杂半分忐忑,片刻才答:“皇后驭下严肃,也不失宽仁,赏罚有度。”
一派官方说辞,崔述轻嗤:“你倒将这套圆滑世故学得一点不差。”
“我是真心的。”周缨没忍住为自己辩驳。
“圣上信重皇后,章皇后此人亦……”
那话却没有说下去,似他对章皇后了解颇深一般,周缨疑惑地盯着他,崔述却只是道:“算是明主,认真做事,自会得到你想要的。”
他将食盒收好:“时辰快到了,先去准备吧。”
“好。”周缨接过来,往外行了几步,又没忍住回头叮嘱道,“好生吃药,朝事再繁冗,身子也是根基,不可怠惰。”
“好。”他极轻地应了一声。
下午授完课,崔述并未急着回府,距离官员下值还有些时辰,他转道去了刑部公署。
薛向在内署接见他,好奇道:“这个节点来访,崔少师有眉目了?”
崔述将那两本簿子搁于案上,不答反问:“薛侍郎抓了户部的几名仓官,不知有无进展?”
“拷问了一番,一口咬定当日确实装载了三万五千石粮,与太仓出入库记录核实无误,倒让我迷惑了。”
他身上还沾染着淡淡的血腥气,应是刚从牢室出来,坐久了闻着便有些刺鼻,崔述眉间轻轻蹙起。
薛向观他神情,低头看了看手背上未及清理的血沫子,召来小吏呈上帕子慢条斯理地擦着,戏谑道:“听闻崔少师先任此职时,最厌刑求,凡事只以证据为要,物证为主,人证次之,一时朝野之中赞誉不绝。
“然而最后却栽在苦主口供上,翻供重审,证物一新,亲谳结论全部推翻,甚至因此获罪,堪称给刑部上下的一记当头棒喝。”薛向笑道,“这世间刁民蠹吏甚多,唯有震慑之道,最快,最可靠。”
话不投机,崔述淡道:“条法之下,薛侍郎自便。若有逾制,自也难逃弹劾制裁。”
“崔少师教诲,下官必当遵行。”
崔述这才打开那本漕河日志,将周缨之言相告:“装订线有异,此簿用宁州产五股明丝线,而非京郊所产六股净蚕线。京中公文簿册皆为后者,薛侍郎可任取几册来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