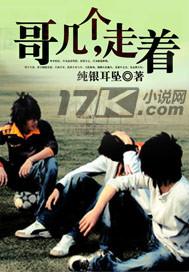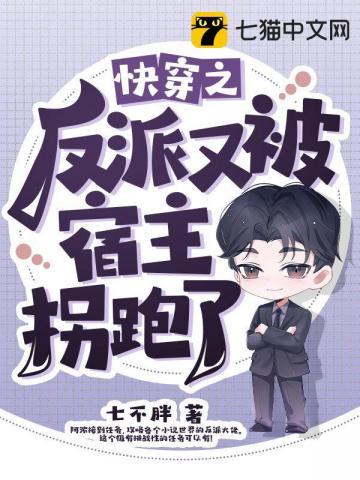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80年代动画片神笔马良 > 170180(第1页)
170180(第1页)
第171章拐卖火车轰隆轰隆地开进隧道,中间有……
火车轰隆轰隆地开进隧道,中间有一段路多山,震得闻慈耳朵疼。
一进隧道,窗外就变得黑漆漆,什么也看不清,闻慈趴在车窗上好奇地盯着,想看看有没有传说中的蝙蝠之类的生物,余光里一闪,她侧头,发现是对面的小女孩也凑到窗边。
“姐姐,你看什么呢?”被妈妈叫做囡囡的小女孩问。
她好奇地把小脸贴在车窗上,鼻子都被压扁了,但也没看清外面到底有什么。
闻慈笑道:“就是不知道有什么,我才看嘛。”
话音刚落,周遭猛然一亮,隧道外的天空因刚才的黑暗而显得格外明亮,淡粉夹橙的晚霞铺满在天空那头,闻慈歪着头看,觉得有种自己正在驶入世界尽头的错觉。
囡囡从裙子的小口袋里摸出闻慈给她的糖,含进嘴里,鼓着腮帮子,瓮声瓮气地说:“这个糖好好吃,和大白兔一样好吃!”
闻慈看了眼糖纸,笑道:“这个是草莓味儿的。”
“草莓?”囡囡歪头,“草莓是什么?我没吃过草莓。”
闻慈就跟她解释了下草莓这种水果,现在交通没那么发达,反季节培育的水平也有限,天南海北的蔬果很难同时出现在一家店里,一个孩子没吃过草莓再正常不过了。
她妈妈孙同志回来的时候,就见囡囡都坐到人家床上,贴着人家聊天了。
“哎呀,囡囡,你怎么打扰姐姐呢?”孙同志很不好意思,把湿淋淋刚刷干净的饭盒放到小桌上,要把囡囡拉回来,“囡囡平时就话多,这次回老家没人陪她说话,全攒下来这会儿说了。”
话里说得是抱怨,但语气分明是柔和甜蜜的。
囡囡果然一点不怕,抱住闻慈胳膊,“姐姐给我讲草莓呢,”她伸出舌头,给妈妈看上面的糖块,“姐姐给的糖是草莓味儿的。”
“草莓?”孙同志一愣,草莓这些年的确不多见,她只勉强见过酸酸的野草莓。
孙同志问闻慈:“听你的口音,是北方人吧?”
“是啊,我是北省人,”闻慈笑道,“就是好长时间没回去了。”
孙同志看闻慈的年纪不大,跟隔壁家的妹妹差不多,但这个月份能坐硬卧跑这么远的路,恐怕是公家出差的,于是笑着问:“你是什么单位的啊?我看着像搞文艺的。”
“哈哈,”闻慈笑起来,“我这会儿没单位,还在上学。”
孙同志顿时惊讶起来,“大学?!”
见闻慈点头,她的眼神变得更敬佩了,“你真厉害!”这点年纪,哪怕在这两届的大学生里都是小的,不过这么一想,她觉得很奇怪,四月不正是春季学期吗?要不是因为这,学校那边没法请假,她丈夫也不至于让她一个人带孩子来老家。
孙同志心里这么想着,却没问,她和闻慈才是萍水相逢,查户口干嘛呢。
她擦干手上的水,从下铺上的包里翻出一把黄澄澄的枇杷来,递给闻慈,“你尝尝,囡囡奶奶家那边枇杷树特别多,那边的川贝枇杷膏也特别有名,味道很好。”
闻慈道了谢,只拿了一个,被孙同志又硬塞了两个。
孙同志又给囡囡塞了两个,自己拿着剩下的一个坐回位子上,细细地剥皮,口中道:“现在大学就是最好的单位,大学生,哪怕只是大专的都比工人好呢。要不是我以前成绩就实在不好,第一次没考上,我肯定是要复读的。”
囡囡嘴皮很利索,立即捧道:“那我给妈妈削铅笔!”
她还以为上大学也要和她一样,在田字格作业本上写大字,还要削铅笔呢。
孙同志扑哧一笑,闻慈也被逗乐了,“你怎么这么可爱。”
囡囡嘿嘿一笑。
孙同志虽然没考上,倒也不怎么落寞,总归她家里条件不错,有底气,现在回城了不也是有个闲散工作的吗?她继续说:“现在我是在国营饭店上班,闻同志喜欢吃沪市菜吗?我们家从我姆妈到爸爸都是厨子,老一辈也是,但感觉这工作也不怎么舒服。”
闻慈好奇:“为什么不舒服?”
孙同志没隐瞒,这些话跟别人她是不说的,但对于火车上初识的陌生人,反倒没有那么强戒心,她道:“我从小跟我妈妈学白案,但进了国营饭店,也就是当个服务员,帮忙点菜收钱,连后厨都进不了——饭店的大师傅都是有几十年资历的。”
她就算借着家里关系进了饭店,哪怕做得再好,也不能上手。
闻慈恍然大悟,一下子明白了。
“那你以后是想自己开——嗯,我是说,那你以后是想做大厨?”闻慈本想说她是不是想自己开饭店,转眼想起现在还没有个体商户,顿时把后半句话吞回去了。
不过个体商户是什么时候有的来着?
凭借着稀薄的历史知识想了半天,闻慈也没法确定——1980年?还是什么时候?
孙同志笑道:“我家还有挺多祖上传下来的家传菜呢,但工艺复杂,材料也珍贵,现在几十年没再做过了,”不管是饭店还是自己家,都主张朴素节约,哪有山珍海味可是。
闻慈恍然大悟,这是不是那种说不准祖上还出了御厨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