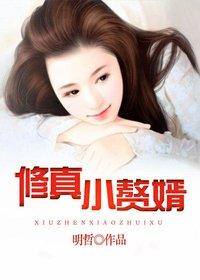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神笔马良是哪个年代的人 > 160170(第28页)
160170(第28页)
工作人员下意识点头,指了下闻慈的方向。
闻慈正思索是拿巧克力蛋糕还是拿草莓蛋糕,面前投来了一片阴影,她下意识抬头,就看到怼到面前的一个录音笔,后面是一个跑得满头大汗的记者。
闻慈站了起来,“你是?”
记者没想到这位叫闻慈的大陆画家如此年轻,但他没有因此怠慢,而是语气客气地问道:“请问是闻慈小姐吗?你上个月,是否在东京的华夏现代绘画展览上展示了一组组画?”
他一上来就说的英文,闻慈疑惑地看着他,点了点头,“是的。”
记者松了口气,心想自己临时接到消息,紧赶慢赶,还好赶上了。
记者脸上端起笑容,认真解释道:“闻慈小姐你好,我是《港城美术报》的记者孙智,想跟你做一期关于这组组画的独家采访,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吗?”
闻慈扫了眼他的工作牌,这个名字,应该是个大报社。
她点了点头,“可以。”
两人走到桌子那一边的沙发座上,一问一答起来。
记者先问:“闻慈小姐知道这组组画在东京产生的影响吗?”
闻慈摇了摇头,“我只知道似乎有一些报纸刊登了关于它的报道”正因如此,国内媒体才开始认可她的艺术成就,不再是因为人体写生而产生的“美院一个疯子女研究生”称号。
记者说:“你这组组画,在东京掀起了非常大的影响,很多画家都在讨论这组组画的风格、技法,称它是具有‘华夏油画史上纪念意义’的一组作品。”
闻慈听得一愣一愣,脚趾抠地,“是、是吗?”
记者严肃点头,“当然。”
《港城美术报》的记者具备相当的媒体和艺术素养,甚至说起那五幅组画,也能侃侃而谈,也许因为是正经艺术媒体,并不像闻慈印象中的娱乐小报那么疯癫,每个问题都是考究而专业的。
她答了许多问题,因为记者的态度,不自觉也严肃起来。
记者经过闻慈的同意后,一直拿录音器记录着两人的问题,这是以免忘记细节,毕竟今天场合特殊时间紧张,没有让他详细记录的机会。
过了二十分钟,记者的采访本已经翻到了结尾,他看了一眼,露出一个放松的笑容。
“感谢闻小姐的配合,”记者起身,主动跟闻慈握手。
他说:“我们报纸是周报,这一期是明天刊登,请问闻小姐何时离港?要是来得及的话,我们愿意送几份报纸给闻小姐。”
闻慈站起来跟他握了手,笑着点头:“那就麻烦孙记者了。”
孙智又给闻慈拍了张照,他还要回报社加班,为了让新鲜出炉的报道变成稿子放到明天的板块上,他再三感谢闻慈,没有因为他冒昧的打扰拒绝采访,然后快步离开。
等孙智走了,闻慈刚端起小蛋糕,张安华就走了过来。
她十分诧异,“你还画油画?”
“嗯……”闻慈耸肩一笑,“其实我现在主要是画油画来着,有空的时候才画绘本。”
张安华惊奇地看了她好半天,最后无话可说,竖起大拇指,“厉害!”
她又凑近闻慈耳边,低声笑道:“刚才他们都看呆了。”
闻慈莫名有种装到了的感觉。
世界上很多行业都是有鄙视链的,未必合理,但它确实存在,就如同艺术绘画看不起商业绘画,而儿童绘本大多是不属于艺术绘画的——它很难被挂到顶尖美术馆的墙壁上,供来来往往各种肤色的人们欣赏、瞻仰。
晚宴差不多结束,闻慈从张安华车里取了外套,就打算回酒店。
酒店的服务很好,闻慈提前约了包车,她裹着外套钻进车里,车子开出灯光闪耀的街道,她透过窗外望着外面的灯火明暗,明明是一样的面孔,但似乎又不太一样。
来自地域、阶级、肤色、外貌……所有差别似乎都可以分出高低,让人比量指点。
但明明大家都只是会思考能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而已。
有什么差别呢?
闻慈漫无目的地扫视着外面的街道,经过一条巷子时,里面的路灯似乎坏了,巷子里黑黑的好像有许多人影,她隐约看见,其中交错混乱,像是正在打架。
她正要收回目光,看到巷子里走出一个男人。
他从黑漆漆的小巷里走出来,走到路灯和月光能照射到的范围里,阴影里的脸一下子被照亮,高挺的鼻梁、饱满的唇,甚至左脸上那个不太明显的酒窝,都一览无余。
闻慈错愕地趴到车窗上,徐截云?!
他头发长得很长,嘴里咬着根烟并没有吸,这么冷的天,也只穿了件薄薄的夹克外套,此时右边袖子似乎还被划破了,露出里面熟悉的蜜色肌肤,月光里沾着血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