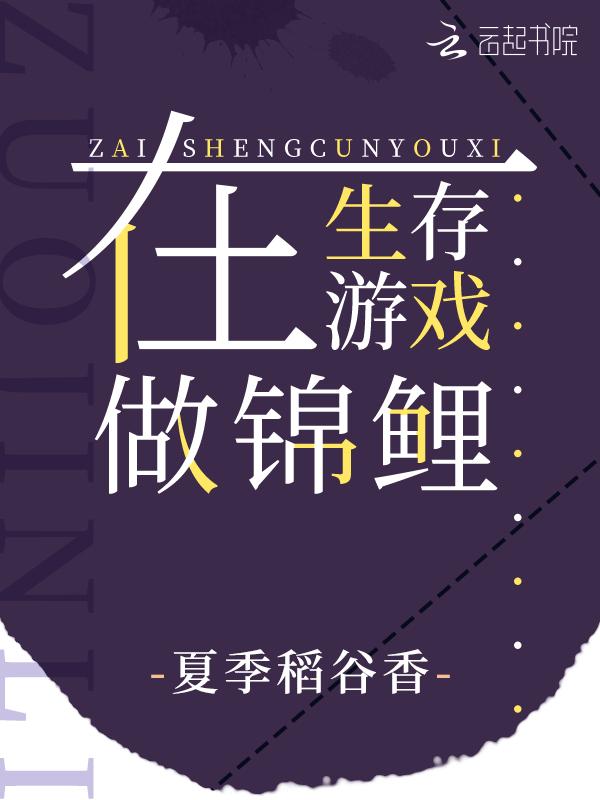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一吻之遥by狐狸宝贝免费阅读 > 第60章 First Kiss(第2页)
第60章 First Kiss(第2页)
蒋成心开始有点慌了,瞥见走廊尽头的绿植外似乎有程煊的身影,挣扎着扭头往那头叫了一声:
“……喂!程……唔!————”
嘴唇上蓦地传来一阵柔软而湿润的触感,仿佛被什么东西轻轻地含住了。
声音像被粗鲁拽去的电话线,断了。
蒋成心在黑暗里睁大了双眼,喉咙仿佛被石头堵住,连正常的呼吸都忘了是什么频率。
为什么?
他很想发问。
为什么他想要的时候他不给,不想要的时候他又给了?
梁以遥摘了眼镜,偏过身将他整个人挡在自己的阴影里,捧住他的脑袋深深地俯了下去。
蒋成心触电般地一抖,仿佛被毒蛇在心坎上咬了一口,血液霎时沸腾,心跳也跟着加速,连脉搏都在额角突突跳动起来。
那人的鼻子戳着他的脸颊,嘴唇贴着嘴唇,舌尖缓缓地在上颚划过,轻轻一舔,仿佛把脊梁都酥碎了,激起一阵深入骨髓的颤栗。
蒋成心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他不堪忍受这种致命的温柔,终于发了狠心在那人的唇上用了劲,咬破了嘴皮,直接见了血。
而梁以遥只是睁开眼看了他一眼,松开了嘴唇,似乎转头做了些什么,随即又以一种不容抗拒的姿态将唇覆了上去。
蒋成心被迫仰着头,舌尖突然感受到一丝冰凉的异样触感,等察觉到那是什么以后,忽然猛地瞪直了眼,开始拼尽全力地推拒挣扎起来。
梁以遥按住他的手腕,低下头吻得更深,好让那股黑加仑和朗姆酒混合的味道在他的口腔中充分蔓延。
“……梁————”
没等蒋成心喘过气,下巴又被那只手稳稳地托了起来,那种冰凉的烈酒已经借由第二个吻灌进了他的胃里,下一秒五脏六腑便像泼了油似的旺烧起来。
那种混合着甜蜜味道的晕眩感袭上了脑袋,让他看不清面前之人放大的脸。
梁以遥被拳打脚踢后依然纹丝不动,睫毛倒是因为动情而微微地颤了颤,手掌摸着汗湿的后脑勺,狠命地揉了揉。
他第一次放任了自己的失控。
不知过了多久,黑加仑朗姆的玻璃酒瓶一滴不剩地空了。
蒋成心猛地推开压在身上的人,连脖子都已经红透了,他踉踉跄跄地往吧台走去,整个世界仿佛在眼里分裂、颠倒、旋转……
“先生?先生?您没事吧?……”
恰好一个服务生打扮的酒保路过,将摇摇欲坠的他搀扶起来。
蒋成心想说话,想离开这里,但他的舌头仿佛和大脑一起麻痹了,张开嘴只能含糊地发出“呃、呃”的声音。
“我……”
话音刚落,整个人便被另一双手揽了回去,后背贴上了一个热度惊人的胸膛。
失去意识前,他恍惚听见那人温柔的声音:
“没事,这是我朋友,他有点喝醉了。”
“……我想先带他回房休息,嗯……怕他吐在这里,可以告诉我电梯在哪个方向吗?”
“……”
梁以遥把闭着眼睛的蒋成心打横抱起来,摸了摸他的额头,脸上的神色安然而放松。
按下电梯楼层的一瞬间,一只手堪称蛮横地扒开快要合上的电梯门,一双阴沉沉的眼睛从外面射了进来:
“你站住。”
程煊刚才在卡座上枯坐了好久,也不见蒋成心回来找他,顿时觉得兜里的身份证和房卡有点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