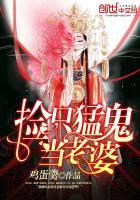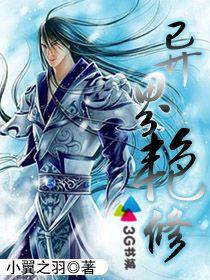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公主永嘉行期一讲的什么 > 3040(第3页)
3040(第3页)
得知孩子被取名秦焕,还被留在王府,她松了一口气,留在王府总归有门有户又锦衣玉食,比不知道送到哪个庄稼户里过得更好。
只可惜她来不及给他做更多的衣服,他不曾看过一眼自己这个娘亲。
或许这样也好,记不得,他才能在王府过的更好,她如此安慰自己,背起包袱离开。
到了院门处,沈嬷嬷忽然跑来,对她道:“老夫人开恩,临走时去看一看孩子吧。”
她跟着沈嬷嬷来到老夫人住处的耳房,乳母抱着秦焕站在那里,令仪颤着手自乳母手中接过孩子,孩子正醒着,懵懂地看着她,小嘴张张合合。
眼泪不受控制扑簌簌落下,她忙往后撤了撤,免得滴落在他身上,忍了许久才忍下,将孩子紧紧抱在怀里,不错眼地看着,恨不得将孩子的样子刻进眼睛心底。
虽一句话不说,一旁的沈嬷嬷与乳母却看的心酸。
便是不忍心,沈嬷嬷还是开了口:“公主,该走了。”
令仪依依不舍地把孩子交给乳母,转身跪下,朝老夫人正房方向磕了三个头,对沈嬷嬷道:“以后焕儿便拜托老夫人了。”
说完又眷恋地看了一眼秦焕,起身背着包袱离开。
正房里,老夫人看着她的背影,问秦烈:“你打算送她去哪?”
秦烈道:“衙署登记造册,该去哪便去哪,我不过问。”
老夫人叹气:“到底夫妻一场,你若念及夫妻情义,不如将她送回京城,不然且不说她十指不沾阳春水,只说她这副样貌,岂能安稳度日?”
夫妻情分?她说那些话侮辱践踏他的时候,何尝想过夫妻情分?
他不杀她已经是看在孩子的面上,当算仁至义尽。
秦烈道:“她若有造化,自己走回去,我必不阻拦。”
老夫人早就从沈嬷嬷口中得知他们当日争吵,听他话中依然带气,不好再劝。
第32章安居、
一辆普普通通的马车在院外候着,将令仪送到黄州州府的衙署外。
那里已有不少妇人在那里等着,令仪穿着棉布衣衫,用头巾遮着脸,低头走过去,站在她们身后。不时还有人过来,人一多,便熙熙攘攘的,直到衙署里走出来一个小吏,示意大家噤声,现场才渐渐安静下来。
他拿着册子一一点名,点到的人站到左侧去,分到不同的地方。令仪名字靠后,前面走了几波人,终于点到她的名字,她被分到州府城郊的郡县。
和她一起被分过去的有六七十人,大都是妇孺,还有七八个孩童,跟着带路的人一路走回祁县。虽说只花了大半天功夫,令仪却从未走过这么多路,累的气喘吁吁,脚板生疼,她这还只是背了个包袱,再看其他人无不背着被褥行李,却无论稚子还是老妪,无一人叫苦,还颇有些精神奕奕,她也不吭声,只静静跟在后面。
到了淇县,又有里正拿着册子点名,给她们分派房子。
令仪一路浑浑噩噩,待到此时方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到此处。
原来黄州之前先被白莲教占据,又被徐州攻陷,之后再被冀州收复,之前人口已十不存一,秦烈下令,从冀州等州迁数万人过来,虽背井离乡,到了这里却分房分地,因此不少人自愿过来。
令仪随的这一行人,都是在战场上死了丈夫的冀州军遗孀,秦烈之前专门在冀州划了一片地供她们居住劳作生活,不收任何税费,可如今阵亡的战士越来越多,孩子渐渐长大,那土地哪养的了这么多人?且土地乃冀州军私产,只给他们免费耕种。
虽然到了这里便与普通百姓一样,田赋人头税徭役一样跑不了,却能得到自己的田地,还送房子,且对遗孀和伤兵,前五年各项税赋减半,于是趁着这机会,不少人报名来了黄州。
和令仪说起这些的,是她的新邻居周嫂,她丈夫追随秦烈的大哥一起死在守城之战中,给她留下一个遗腹子,和一个老母亲。
经历这般苦难的妇人,却不改其热心肠,自己麻利收拾好东西,做好饭菜,见到隔壁一点动静没有,土墙矮的狠,一勾头看到令仪只一个包袱,连锅碗瓢盆都没带,便热情邀请令仪来自家吃饭。
待令仪吃完饭,她又带令仪去其他相熟的遗孀家里买多余的被褥,帮令仪铺好了床,才回自家去。
翌日一早,周嫂又来叫令仪去她家吃早饭。
令仪习惯了锦衣玉食,盖着那泛着潮气的粗布被子,昨晚睡得不好,可今日要去选田地,耽误不得,只得勉强起身。
周嫂家早伤吃的黑窝窝和玉米糁,令仪勉强吃了一些后,与周嫂一起去里正那里,待到人齐了一起去选田地。
走了一个多时辰,方到一片荒草胡阔处,里正痛心疾首:“这里以前都是良田,虽经历了大旱,前年也被我们救回来大半,可惜后来打了一年多的仗,又全荒了。不过只需一两年便能养回来,按着人头算,不管老人小孩,一人十亩,自个儿挑好了来我这领田契。”
令仪完全不懂这些,只跟着周嫂。
周嫂蹲下拈起土搓了搓,又在鼻下闻了闻,面露喜色,“真是上等田!”
她家三个人,便是三十亩地,冀州田税本就不高,前五年又减半,除非遇到大灾年,否则一家人不仅衣食无忧,年底还能存下银子。
分给将士遗孀的全都是以前的上等田,没什么可挑的,周嫂很快选好,问令仪:“妹子,你选哪块?”
令仪出了王府,便一心想回京城,根本无心在此逗留。
闻言只道:“我不懂这些,都听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