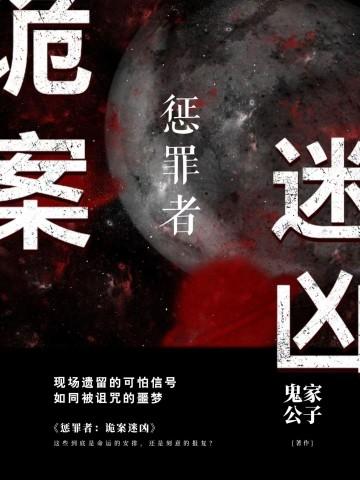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三国之汉魏风云笔趣阁 > 西园文学会5(第2页)
西园文学会5(第2页)
岂不常勤苦?羞与黄雀群。
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
慷慨赋诗毕,刘桢投笔,再灌烈酒一杯,陈词论道:
“其一,吏服雅训,儒通文法,此汉士风骨之实也。士学君臣、朝廷、三事之纪。文法典艺,具存于引。至乎末世则不然矣,执法之吏不窥先王之典,搢绅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笔之吏,岂生而察刻哉?起于几案之下,长于官曹之间,无温裕文雅以自润,虽欲无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岂生而迂缓也?起于讲堂之上,游于乡校之中,无严猛断割以自裁,虽欲不迂缓,弗能得矣。先王见其如此也,是以博陈共教,辅和民性,达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雅训,儒通文法,故能宽猛相济,刚柔自克也。”
“其二,欲论风骨,必言君子崇德无私。盖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乎存政,存政莫重乎无私,无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笃其志而后行。然则动者吉凶之端也,语者荣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几也,行者安危之决也。故君子不妄动也,必适于道;不徒语也,必经于理;不苟求也,必造于义;不虚行也,必亩于正。夫然,用能免或击之凶,享自天之佑。故身不安则殆,言不顺则悖,交不审则惑,行不笃则危。四者存乎中,则患忧接乎外矣。忧患之接,必生于自私,而兴于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济其欲,理之至也。”
“其三,风骨清谈,士当务本为重。古者之理国也,以本为务。八政之于民也,以食为首。是以黎民时雍,降福孔皆也。故仰司星辰以审其时,俯耕籍田以率其力,封祀农稷以神其事,祈谷报年以宠其功。设农师以监之,置田畯以董之。黍稷茂则喜而受赏,田不垦则怒而加罚。都不得有游民,室不得有悬耜。野积逾冬,夺者无罪;场功过限,窃者不刑:所以竞之于闲藏也。先王籍田以力,任力以夫,议其老幼,度其远近,种有常时,耘有常节,收有常期,此赏罚之本。种不当时、耘不及节、收不应期者,必加其罚;苗实逾等,必加其赏也。农益地辟,则吏受大赏也;农损地狭,则吏受重罚。夫火之灾人也,甚于怠农;慎火之力也,轻于耘秬。通邑大都,有严令则火稀,无严令则烧者数,非赏罚不能齐也。”
三番论说,刘桢把风骨三大核心要义阐释得清楚明朗,比卢毓的更系统完整。崔缨早就听得不知魂魄何往了,只能跟着周围欢贺的人群,不停地拍掌。谁知,刘桢还有最后总结一段,反驳卢毓选官只看贤良——
“臣闻明主之举也,不待近习;圣君用人,不拘毁誉。故吕尚一见而为师,陈平乌集而为辅。
“臣闻记功志过,君臣之道也;不念旧恶,贤人之业也。是以齐用管仲而霸功立。秦任孟明而晋耻雪。
“臣闻振鹭虽材,非六翮无以翔四海;帝王虽贤,非良臣无以济天下。
“臣闻观于明镜,则疵瑕不滞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
“臣闻孟圣云:‘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嗟夫!士执乾灵之贞洁,禀神祇之正性,外清内白,如玉之素,若鹖鸟奋翅,抗青冥而不旋反也。然选官择才,岂可拘于俗规,偏执一段?风骨良臣,自古有之,唯伯乐难觅也。
……
到场文士,但凡通晓笔墨,都清楚刘桢这最后一击,采用了流行的文学体裁“连环”,论证的含金量有多高。再加上刘桢快人快语,一席话如电闪雷鸣,与赵壹《刺世疾邪赋》有得一拼,四座皆惊。卢毓叹服不已,连连笑说才不及也。
不论是曹丕还是曹植,都兴奋不已。不过,他们似乎不在乎卢毓和刘桢的辩说孰优孰劣,兄弟俩不谋而合,聚在那张写满咏物诗的布前,窃窃私语,喜不自胜。
崔缨笑了。刘桢啊刘桢,这诗人的身份,真给你在文坛开挂了。
就这样,刘桢以压倒性优势,赢了卢毓。连曹丕的玉箸也投给了刘桢。
卢刘二人作揖,拜谢还席。
眼见着亲近曹植的文士三局两胜,赢了自己。曹丕也不恼不急,唤来五官中郎将文学徐幹道:
“伟长兄,今日之辩,犹未尽兴,先生博学多识,著述颇丰,对当朝制度了然在胸。烦请先生上台,出一命题,不失公允。”
徐幹称喏,眼底风平浪静,接过崔缨递来的卷牍。
曹丕的意思,到底还是要徐幹,从预先准备好的诸多辩题名目中挑选一个,譬如“出世与入世”,“奸邪善恶之辩”,“君臣矛盾”,“宗法嫡庶”等等。毕竟徐幹善论,在邺城小有名气,又是将府文学官。徐幹略瞟了几眼,便倒吸几口凉气。
这些辩题,背后暗藏曹丕深沉用意。徐幹不想去揣摩,也不想掺和进他们兄弟二人的文争。只能推脱道:
“是古非今,君子不为也。中郎将委命,臣诚惶诚恐,不敢妄言朝制。幹虽不敏,以为日将西倾,莫若‘封建论’为辩。自始皇改分封为郡县以来,历代君臣多有论述。此论当合众心。”
封建论,封邦建国。也就是老生常谈的郡县制和分封制之争。这个命题,可以谈论先秦两汉得失,可以谈论汉末郡守割据地方,避免站队丕植党任何一派。徐幹献完此计,便隐身退回席上。
曹丕虽不悦,但只能由他。于是郑重地跟喧嚷的群臣公布了这个辩题。
“封建论?”曹植惊叹,想都没想,就嬉皮笑脸,举起酒觞,往南坐席而去。贴在他府上的文学掾司马孚身侧,敬酒邀他出战。
崔缨听不清曹植等人聊了些什么,回头却见,曹丕将目光投向宗室席座那边。显然,就目前的形势来看,这兄弟两个,都默默地想在暗中较劲,都想让自己幕府的文士夺人先声,在文坛占据话语权。
司马孚是司马懿的胞弟,学识渊深,比刘桢更为知名。这一轮,曹丕不好请司马懿出面。可宗室席座里,文学掾夏侯尚不在,夏侯楙又是个半吊子,夏侯称又尚武为主。繁钦路粹等人,能比得过司马孚吗?
正犹豫间,见吴质上前,给自己献策道:
“颍川阳翟人郭奕,可为公子一辩。”
曹丕挑眉:“那少年幼弱,如何能辩。”
吴质便把往常郭奕、荀恽二人的辩论说了一遍,又加一句道:“荀恽与平原侯亲善,恐不能为公子所用。公子当年为郭奕其父治丧有恩,他又是公子伴读。今日之后,定当为公子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