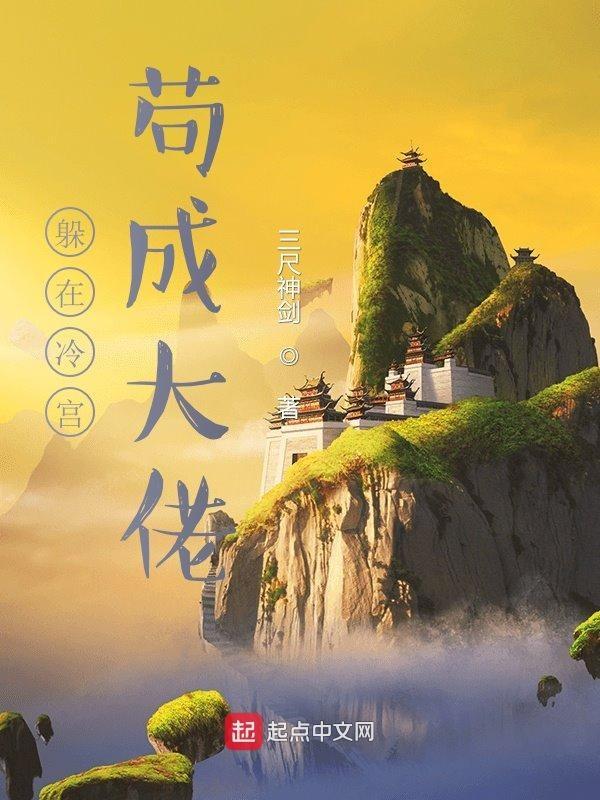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仙君总想救赎我免费阅读 > 重生之我在周家当家主(第1页)
重生之我在周家当家主(第1页)
奚九牵起嘴角,似嘲似叹:“我还以为此路不通,谁知五姨娘却凭一件婢女衣裳,猜到给她递纸条的人必会去找季曾芸。”
“我刚与季娘子碰头,她便带着周家少爷第一任妻子的血衣来了,不仅施以援手,更将计就计,提议把吓晕的周怀述塞进他儿子的棺材里。”
“如此一来,等他明日清醒,发现自己与死去的儿子同棺而眠,怎能不信冤魂索命,鬼神报应?”
她的眼中闪着光,对五姨娘的智慧和狠劲颇为佩服。
“她比我们更了解周怀述,更知道什么才能真正击垮他。”
她抬眼看向晏祈:“我原想着,让你来搅浑这摊水,若可以当众揭穿他儿子已死的真相,这便是一步好棋。万万没料到,他竟狗急跳墙,敢在酒里动手脚。”
“凡间迷药于我无用,演给他看罢了。”晏祈姿态仍旧倨傲,但也不吝夸赞,“倒是那位五姨娘,确有几分急智与胆色。”
能在周家那种地方隐忍至今,绝非寻常女子。
若非五姨娘及时示意家丁将他带离宴席,又安排人“照料”醉倒的周老爷,为他们腾出施展的空间,今夜之事,绝不会如此顺遂。
“就待明日了。”奚九望向窗外沉沉的夜色,期待着黎明后的又一场好戏。
天刚破晓,周府上下还在酣睡,晏祈便在这样一个万籁俱寂的时刻,推开了东厢房的门。他丝毫不见外客的拘谨,反倒像是这府邸的主人,径自便要往内院方向去。
两名守在廊下的家丁正倚着柱子打盹,晏祈行至他们身侧,修长的指节在家丁耳边的廊柱上,重重叩了两下。
其中一个家丁猛地一颤,惊醒过来,另一个也跟着晃了晃脑袋,两人睡眼惺忪,兀自揉着眼睛。
“你家少爷,住在哪。”
“西……西苑啊。”
那家丁脱口而出,哈欠刚打到一半,像被鱼刺卡住,连滚带爬地站直了身子。
“晏、晏医师?您起怎么这么早。少爷、少爷定然还在安睡,您看是否先用些早膳?”
“既病了,便该积极诊治,岂有因贪睡延误的道理?”晏祈脚步不停,扫过一排岔路,随手一指,“那该是这边。”
仆役们不敢对他无理,又不敢真放他过去,只得小跑着跟在他身后,连声劝阻。
“晏医师,少爷还没醒,不急的,不急的……”
“你们自然不急,你们少爷急啊。”晏祈行至一处回廊,在一扇雕花木门前停下,作势便要推门。
“不是这间!”
跟在最后的一个婢女,几乎是扑上前来,慌忙拦住。
“既然不是这间……”晏祈从善如流地收回手,带着猫捉老鼠般的戏谑,随即身形微转,正正对上了紧邻的另一间屋子,“那定然是这间了。”
“吱呀”一声,清晨微光争先恐后涌入屋内。素白的幡帐高悬,正中横着一口黑漆漆的棺材,空气还中弥漫着烧过纸钱的呛人味道。
所有试图劝阻的声音戛然而止,仆役们呆立门外,面上交替着惊恐与茫然。
五姨娘恰在此刻赶来,她发髻微乱,像是闻讯刚从榻上起身。她一眼瞧见伫立门前的晏祈,脸上立刻堆满恰到好处的惊慌,以手掩口,失声低呼:“呀!这、这是……!”
晏祈的语气也带上了恰到好处地惊疑:“这不是你家少爷静养的院子?这棺中所殓,又是何人?”
还未有人给他做解释,棺中,突然传出一阵沉闷的声响。
咚……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