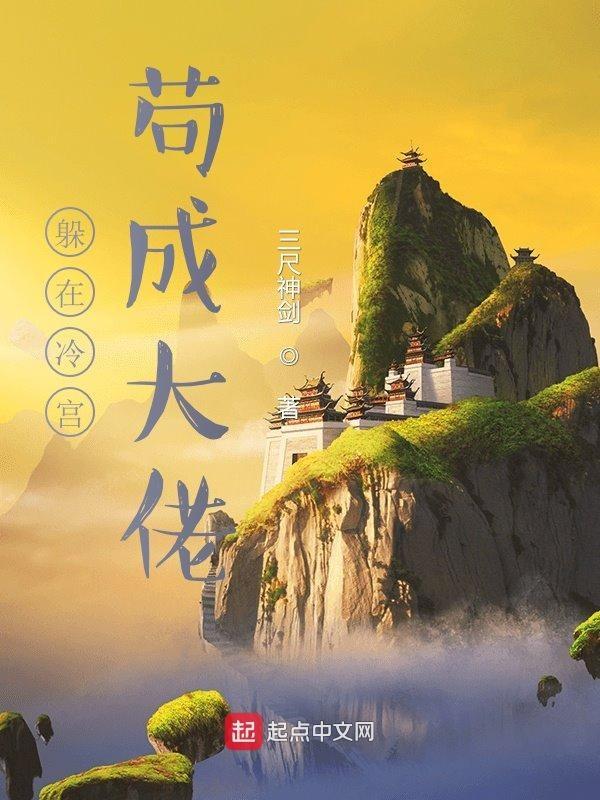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和嫡妹换亲三年后怎么样了 > 第 3 章(第2页)
第 3 章(第2页)
撕心裂肺的咳嗽声,响彻寂静小巷。
一口血吐了出来,染红了衣襟。
两个丫鬟显然已经习惯了,丝毫不见慌乱,有条不紊地帮时乔顺气,擦拭血污,帕子脏了一块又一块。
吴妈妈面露不忍,夫人自受伤后便时常咳血,看着倒似短命之兆。夫人规矩虽学得不好,待老爷却是真心实意地好。这样的人,怎落得如此下场?
待咳嗽声停了,她语重心长道:
“夫人若是和离,您这副情形,以后想找个更好的归宿怕是难。天下男子大致都是一样的,任谁也不可能一辈子只守着您一人……”
时乔落下帘子,“何七,走吧。”
“是!”
何七扬鞭,马车辚辚而去。
马车里,小荷觑着时乔,憋了许久,还是忍不住问:“姑娘,那位裴二爷,当年要求娶的当真是您?”
不怪小荷不信,连时乔也不敢相信。
她和那裴二爷素不相识,第一次见他还是在进京后的宴会上。
那位裴二爷在一众王孙公子中脱颖而出,不但文采斐然,武艺骑射也是一流,再兼容貌俊美近乎妖孽,一场宴会下来,不知俘获了多少少女的春心。
彼时她感觉此人过于张扬,生怕旁人不知道他有多少本事一般,且还爱在她们跟前晃悠。
在她因做不出诗被贵女们嘲笑时,他还曾为她解围:“会作诗就瞧不起种地的?我很好奇,若把诸位和她一同扔到荒野中,谁能靠着‘作诗’活下来?”
“她会的,是活人性命的真本事。而你们引以为傲的,离了这金堆玉砌的宴会,还剩什么?”
一番话下来,那些贵女的脸色精彩得很。
接下来的宴会,她便自在了许多,再也没有人取笑她这个乡下丫头了。
后来侯府夫人上门提亲,她方知原来裴二爷看中了夏如蔷,那日是在孔雀开屏呢。
在那之后不久,她去慈圭山为母亲点长明灯,告诉母亲她要成亲了,出灯塔时遇到了他。
夕阳下,他屈膝疏懒闲坐意态风流,那敛尽天地英华的眉眼染了霞色,愈发纷华靡丽,摄人心魄。他漫不经心地看了过来,在看到她时,顿时坐直了身子,变得一本正经起来。
他问她:“你还认得我吗?”
那时他和夏如蔷已经在议亲,时乔要避嫌,对他福了一礼,“小侯爷有礼。”便快步离开。
他起身追了上来,认真道:“你别叫我小侯爷,我叫裴临川,表字慎之,外面的那些传闻你别信,我……我定不会负你!”
他说着话,将一块玉佩塞到她手里,那张妖孽一般的俊脸涨得通红。
时乔在宴会上曾听那些失了面子的贵女历数裴二爷的斑斑劣迹。
说他自小聪慧,十二岁就上战场杀敌,皇上也喜爱他,常召他进宫作皇子伴读。只是随着年岁渐长,他日益顽劣,终日溜鸡斗狗,花天酒地,成了有名的纨绔。还曾在赌场与人大打出手,打死人逃出去一躲就是一两年。
时乔本还半信半疑,彼时却发现传言果然非虚,他连未来姨姐都敢调戏。
她将玉佩扔了回去,呵斥了句“小侯爷请自重”就快速跑开了。
回京路上又遇上了他,他骑马经过她的马车时,扬手一挥,玉佩穿过车窗,正正好落到她手边。
她捡起玉佩想还回去时,却见他已远去。
广阔的天地间,少年鲜衣怒马意气风发,扬手挥舞着马鞭,玉白锦袍肆意飞扬。
后来再见他,便是大婚后了,在瑞王府的一场宴会上。垂花门前,她扶着罗珣的手下马车,抬头便看见裴临川站在不远处的松树下,紧抿着唇,直愣愣盯着她,一双眼沉得厉害。
如今想来,裴二爷要求娶的,恐怕确实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