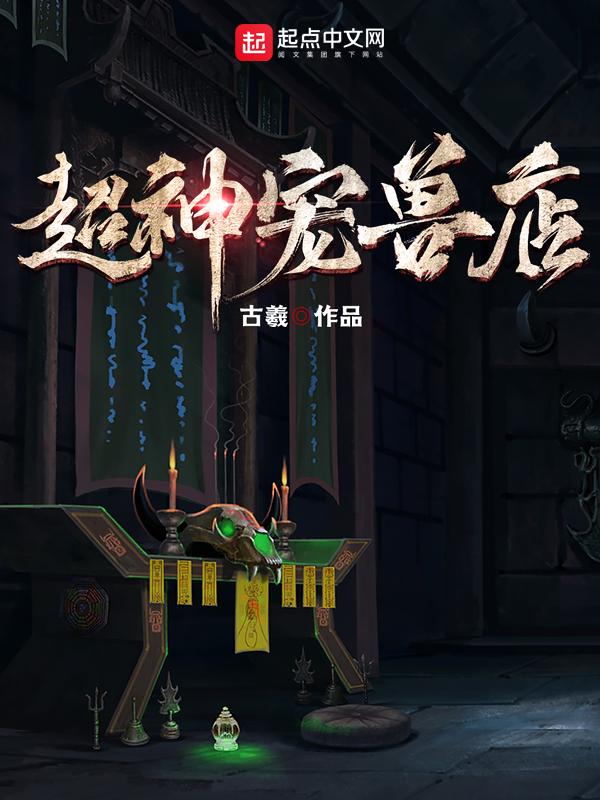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别嫁给我大哥!作者 荷桃粥 > 90100(第12页)
90100(第12页)
“那么你呢?你还在乎吗?”
她侧头看向贺兰澈,或许多亏有男德辖制,或许是人们不敢招惹药王谷——赵鉴锋策划的流言报里,多数还是讨伐和嘲笑他们男子的,自己只是被轻飘飘带过,甚至褒奖。
就像历来的历史,男女两情相悦犯了错,不都是男子轻飘飘揭过,女子失去清白而无法翻身么?
不过这是在晋国,教你们乾坤易位罢了。
“我还在乎。”
贺兰澈的双手还在打绞,他身上的“痴汉”标签从来就没洗掉过,原本只是在药王谷内被揶揄,是赵鉴锋一纸报刊送他举国闻名。只是他比常人幸运,家中祖父祖母,父亲母亲,连带大姑母,顶着万人嘲笑却都不责怪他。知晓他的品性,甚至支持他。
真正不在乎这些谣言的是爱他的家人,而非贺兰澈自己。
于是,贺兰澈重申一遍:
“我还在乎那些流言报。”
“毕竟人最容易难过的,便是太在乎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
“可冤枉你的人比谁都知道你冤枉。”
“他们指指点点,因我们的事而争吵不休,实则,每个人看见的世间事,完全是不同的。”
他靠近她:
“还记得我为你雕的傀儡吗?那堆木头在被刻出你的模样之前,从上方看是三角的,从侧看,又是圆的。”
“只是我有幸能雕出你,横看竖看,每个角度,才都完美圆满。”
“所以,我在乎那些报纸,又如何——他们都笑我,偏偏我最好笑。爱听笑话,那就多笑。”
“他们笑话我们‘三人成行’,我们也笑话乌太师,不是吗。”
“人人都有可笑之处,你我也非例外。”
“可最要紧的是,你不笑我。”
长乐又被他这堆滔滔不竭的话说得哑然,这是贺兰澈难得不逗人的时刻。她本有很多话想回他,却又不知道如何说起。
人在受委屈的初期往往是能凭一腔愤怒强行压下眼泪,顶着脊梁骨与来人对峙,可是一旦有人关心、说理解、说都懂你,再坚强的人,眼泪也会决堤。
可她最难过的事是,没人真正理解她这些年。
她听贺兰澈形容:“人生不仅可以往高处走,还可以到处走。”
可是,大道如青天,独她,不得出。
笑话无相陵,笑话三人成行,笑话乌太师,都是笑话她。
如果贺兰澈有一万次会毫不犹豫地奔向她,她就有一万次不想将他沾上泥,让他发现自己身处的危险,让他碰上毁灭的可能。因为这是她的软肋,她实在是,赌不起。就像赵鉴锋那一战魂烈掌,如果她是理智时,就该明白,自己不该去替,可她还是去了。
而她在偷偷找的那些人,又何尝不是在找她。
任此刻再美好,总有一日要面对,前方未知,行路亦难。
因而,大道如青天,独她,不得出。
她被规定在其中。
……
贺兰澈原是想叫长乐在露台与他多坐一会儿,这里没有戴蘑菇头帽子的人来抓他罚款。不成想,却把长乐聊哭了。
这不是他的本意,他只好轻轻递来帕子,搂过她来安慰:“我不敢帮你擦脸,怕又将你的妆擦花了。但你若不想擦眼泪,多哭一会儿也没关系。只是,你别和林霁讲,我怕他要和我过不去。”
果然,长乐破涕拧他。
城中更鼓四起,楼下喧哗喝止行人,看来到了子夜宵禁之时,京陵武侯卫整肃街道的能力可跟鹤州不一样。
贺兰澈发现了,便道:
“我初从邺城到鹤州去的那个晚上,陪你去旧庙,只道咱们国中严苛,宵禁一刀切。可这京陵宵禁比鹤州晚一些,听说也要取缔,指不定将来就与邺城一样,晚上也能随意四行了呢。”
长乐神经放松下来,就这样靠在他肩头,他顺势拥紧她:“若困了,你就睡会儿,我守在旁边,等你半夜梦魇醒了,再接着讲故事。”
她眼皮耷拉,却意犹未尽:“你不怕蘑菇头又来举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