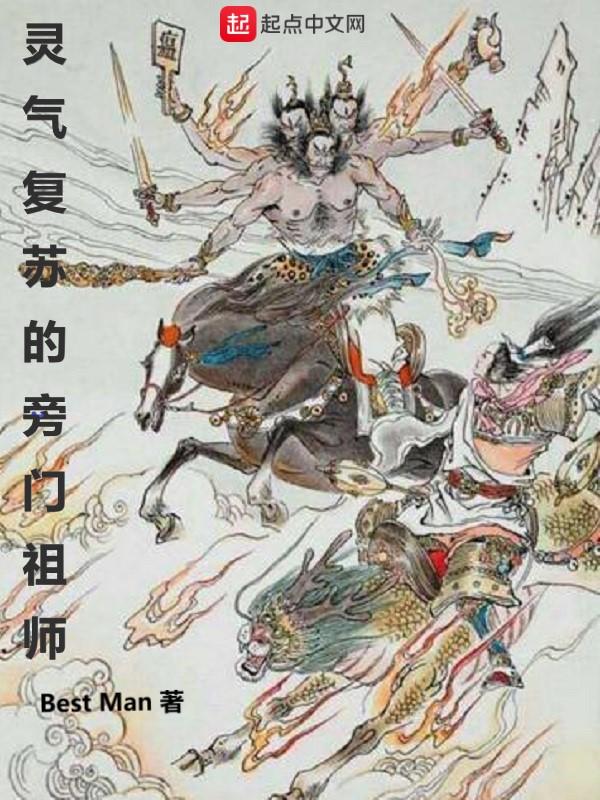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一寸光阴一寸灰 > 第102章(第2页)
第102章(第2页)
“咳咳,咳咳。”先生猝不及防地被戳了心肺,这事他无从否认,只不过世子见到的乃因,重重恶果皆报在他身上,那一整个腊月,但凡出门,他脖子上遮挡痕迹的狐裘就未摘下来过。
明明在说世子之事,怎么就引火上身。
刘霄无奈地喟叹一声,“昨日的功课拿出来。”
“少爷,”晚些时候,福安敲门,“无一大人喊您去雪庐用晚膳,陛下今日也在。”
“我乏了。”
向瑾的房门自内上了门栓,福安推了一下,愕然道,“少爷,您不舒服吗?”
向瑾蔫蔫地,“我要睡了,莫吵。”
福安摸了摸后脑勺,自言自语地嘟囔,“这股子别扭劲何时才能过去啊?”
自日前与杜院判不欢而散,成景泽也不再拘着,恢复了日常作息及出行。
早上又未在雪庐见到向瑾,陛下问,“世子病了?”
无一诧异,“没有啊,您没在的时候,世子从不缺席。”
皇帝:“……”
傍晚,世子又推了晚膳。不多时,无一敲门,“世子,陛下请您过去一趟。”
向瑾从趴俯的桌案上倏地起身,敷衍拒绝的话在口边绕了绕,最终还是咽了下去。跟在无一身后,进了雪庐的大门,暗卫头子朝他努了努嘴,示意陛下在沙盘的房间等他。
向瑾深吸一口气,“陛下。”
“进来。”
向瑾走了进去,未像往日那般行至沙盘跟前,手中也无案卷。
如水的月光透过门缝倾泻进来,正拢在小世子抽条了不少,却依旧有些单薄的身姿上。向瑾半垂首,侧对皇帝,脖颈后侧的那一刻小痣恰巧氤氲在霜白的月华之下,愈发红得鲜活而艳丽。成景泽怔了一刹,秋猎那日高热恍惚中的旧梦毫无预兆地铺陈开来。他蓦地攥紧双手,不知是不是错觉,虎口处似乎震了一下。他瞥过去,沉寂的蛊虫并未移动,一切只是他的错觉,包括那久远的模糊的不堪回首的黄粱梦。
成景泽缓缓吐息,大约是这异域蛊术有些邪门,加上杜院判旧事重提,令他被迫触景伤情,心浮气躁。可无论如何,都不该投射到眼前的少年人身上,哪怕他携带着与他而言这世间仅存的虚无缥缈的慰藉。
小子无罪,怀璧其罪……他哪怕只是一念而过,亦属罪孽深重。成景泽眉头紧锁,强行斩断所有不合时宜子虚乌有的浮思。
各怀心事沉默片晌,陛下问,“世子脚踝痊愈了吗?”
向瑾机械地点了点头,目光始终避开,“早已无碍。”
成景泽问责,“那为何不事晨练?”
为什么,还不是为了躲你远点儿?憋闷了好些日子,少年人叛逆心起……又按下。
“向瑾懈怠,请陛下责罚。”
成景泽愕然,在他印象中,小世子再是勤勉不过,因而无故旷了武科,他以为是受了传言影响,或是对婚配之事有所抵触。荣国公夫人离开之前叮嘱他聊作开解,是以陛下将人喊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