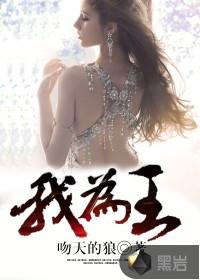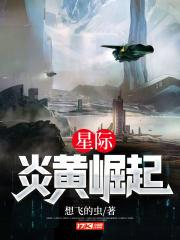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一寸灰乔一帆最后有多强 > 第171章(第2页)
第171章(第2页)
就在监正额头冒汗,忍不住将求助的目光投向谢太傅与瑞亲王之际,陛下点头应允。
老监正腿一软,不知陛下是一时未察那究竟是个什么日子,还是压根不在乎,总之侥幸逃过一劫,弓着身子赶紧退下了。
散了朝,自然又是一番风云涌动,世子与陛下彻底决裂的说法又添一道铁证。
两府联姻忙得礼部官员团团转,这桩婚事的规格仅次于陛下大婚而已。不仅京中数得上名号的达官贵人皆在受邀之列,外放宗亲与边疆大臣,甚至东南西北各方邻邦,亦匆忙赴京。面上轰轰烈烈,不可拂了大晟皇亲国戚的体面,可考虑到陛下立场,又不能过于殷勤,属实为难。
万事俱备,只待良时,众人皆以为能够暂且松一口气时,刘氏突然强势提出,值此普天同庆之日,理当告慰先帝在天之灵。太后亲临养心殿,当着众阁老的面,头一遭据理力争,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
一干老狐狸噤若寒蝉,只敢说些模棱两可的和稀泥之词,是非利害,三缄其口。
一场预料中的针锋相对因着陛下过于轻易的妥协而消弭于无形,不仅如此,刘氏只是提出在宫中大作法事,百官随祭,皇帝却主动将之升格为皇陵祭天大典,专事告慰先帝。
刘氏自然无从反对。
于是,那一日的热闹加上热闹,便敲定了。
刘氏大获全胜,回到慈宁宫,意外地,刘霄求见。
刘霄于轮椅上见礼,“草民给太后请安。”
刘氏心情大好,“免礼,可是世子有何交代?”
“非是,世子并不知草民前来。”
刘氏一顿,目光在刘壤身上转了转,“那是……”
刘壤一揖,“恕草民无礼,太后可是欲以宗亲辖制刘壤?”
皇城乃至京都,禁军势力一分为二,皇帝与太后旗鼓相当。康王行踪成谜,大抵是躲在暗处伺机而动,不大可能携带大军。那么此战关键,便在于京南京北两营,南营归附太后不是秘闻,但刘壤统御之下的北营显然更胜一筹。
刘氏一定会想办法,威胁甚至铲除刘壤。
太后不承认也不否认,时至今日,各方手中大多明牌。她早已通过胞弟,提前困住刘氏旁支与刘壤交好的远亲近属。
刘壤单刀直入,“余以为,在下是更适宜的人选。”
刘氏不语,她的确考虑过,刘家两兄弟那点儿龌龊事,她怎会不知。不过,顾忌着与世子的暂时交好而已。
“刘壤其人,六亲不认,届时未必得用。况且,宗亲人数众多,易打草惊蛇,到底是本家,于太后声望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