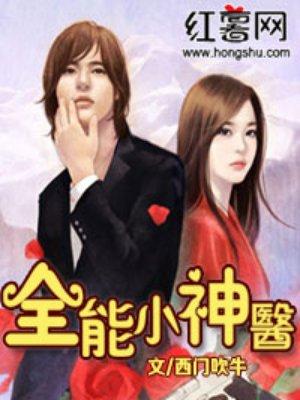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京阙雪芍药与鹿笔趣阁 > 送袖箭(第3页)
送袖箭(第3页)
透过槛窗去看,除了几个光秃秃的枝干,又哪里有人的影子。
秦惟熙莞尔,不禁哈哈地笑起来:“四哥,你也有怕的人?”
褚夜宁面上却丝毫未有恼意,而是语重心长地道:“是敬重。”
他看向被他“圈”在其中的秦惟熙:“秦洛,我想要什么,喜欢什么,我绝不会让你去猜。所以今后任何事,你想要什么,你要做什么,亦不能瞒着我。”
“可行?”
对上那张不真实的面,再透过她那双如同一汪潺潺泉水,清澈见底的眸。蓦地想起那日再不同于年少时青涩稚嫩的面,恍若转瞬变幻出的那张明媚正当韶华的面。
秦惟熙只觉此刻像面前有一只体型硕大的大狼狗在虎视眈眈地看着自己。不知何时额间竟隐隐生出了一丝薄汗。
庭院微风拂起,吹得这间书房内半掩的槛窗咯吱咯吱,开开合合不停。犹如敲打着她的心,噗通噗通,心脏也随着急据的跳动。
“时辰不早了,我还要去接小姝。”她霍地站起身,却已然忘记褚夜宁近在咫尺,在起身的那一瞬间,头顶猛地撞上了他的额头。
褚夜宁躲闪不及连退两步,而后只觉额间疼痛袭来,两眼开始冒出亮闪闪的小繁星。
他抚着额,似倒吸了一口冷气:“嘴不饶人还要暗害于我。”
秦惟熙忽然想起一事,转身问:“那姚子竹如何了?”
褚夜宁闻言忽而面色一凝,随后看似漫不经心地道:“乱咬的牙掰了,扔进粪坑里待了一夜,现下老实着。”
“什么?”
褚夜宁再是狡黠一笑:“与你说笑的。”他又招招手:“秦洛,过来,四哥有一样东西要给你。”
见她在原地不动,他便去一面墙壁前的多宝格上取下,窄长的盒子打开,竟是袖箭,很是小巧。
“秦洛,用来防身。但今后有我在,你一定用不到。”他唇角带着笑意,很是认真的盯着她看。
秦惟熙眼睫一颤,又听得他低笑了一声,再道:“勿要再磨簪。”
她抬起头,随后看向那放着琳琅满目瓷器的多宝格,适才他去取袖箭时,她看见那格上的最顶端放着一个朱红色的木匣子。那匣盒上浮雕着云纹花样,她最熟悉不过。是那年他随褚伯父出征前,她亲手所送的大阿福,而后他送给了她一个小香毬。她当时以为晚了一步,以为他早已出了城,再见面时候兴许就是新岁之际,便让秦府的车夫加快了速度。
年少的时候,父亲的书房里有一架多宝格,上面放着许多父亲最喜爱的古玩器物,父亲每日都要拿着帕子将那格上的尘灰擦得一遍,再将母亲送与他的一把宝剑放到最顶层。
当年父亲两眼仿佛天际的繁星,明亮又璀璨,嘴角漾起丝毫未曾隐藏的笑意:“这多宝格的最上层啊,是为父心尖之物,是为父最是珍贵的宝贝。”
所以这些年,京师转瞬十个春夏秋冬,即使他当年远去了边关征战,又如雀舌所说,他重伤回京,雪水饱腹,路上跑死了一匹又一匹的马,再到他远去了西北,流放十年久,这匣盒内的泥娃娃,他一直都有在保留着。
她疾步走过去,踮起脚伸长了手臂去取那匣盒。却碍于这古架竟比一些身形修长又高大的男人还要高。她再努力踮起了脚尖,指尖也只能碰到那匣盒一角。
身后忽而响起一声低笑,紧接着有一只手伸出将那朱红色的匣盒取了下来。随后他打开那匣盒,双手捧给她看,微微勾起唇角:“是想看个究竟?”
她不假思索地端正了那匣盒,见盒子内果然是她当年所送,那寓意极好的大阿福。正想取出细看,余光一瞥,却发觉她的两手不知在何时竟与他的两手牢牢相贴,一同捧住了盒子。
她眼睫一颤,蓦地一松,却在那一刹那有所觉,他的双手是那般的冰凉。
适时,外间有脚步声响起,二人再听得一声轻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