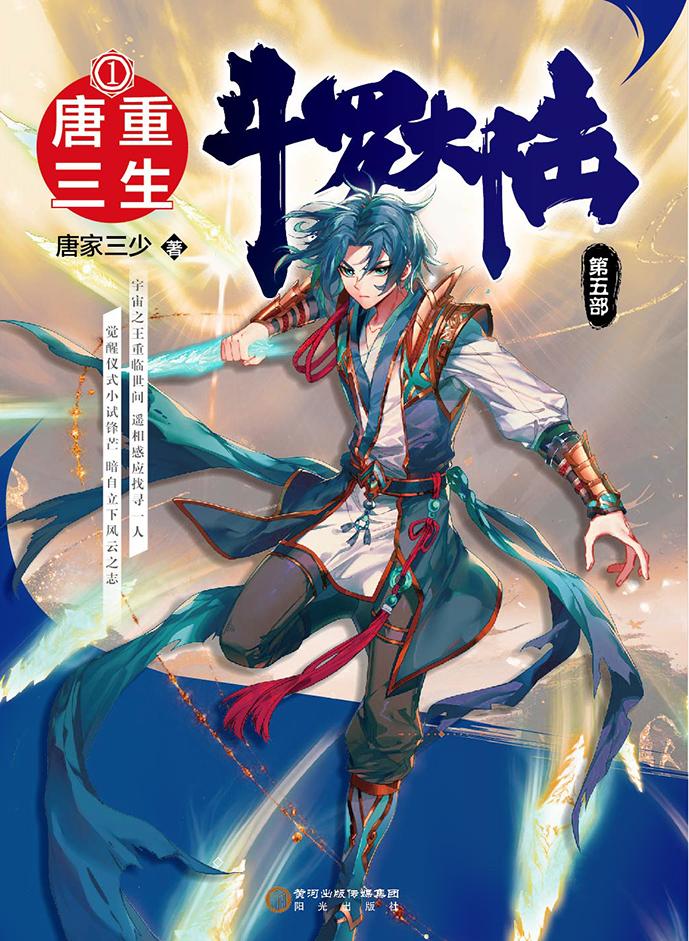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春山归远全文免费阅读 > 5060(第16页)
5060(第16页)
老人佝偻着腰打开一个大木柜,在里头翻了半天,拿出了两本泛黄的册子,却比方才的要薄了许多,递给管事汉子。
这一次再仔细翻找,居然还真的找到了,登记的果然是魏简常这个名字,酒窖是他花了一百五十两银子买下来的,这笔钱在舒夜这种边陲之地可不是小数目,带女流亡各地的孟远亭竟能出手这么豪阔,看来他在离火教的那些年,实在是攒了不少家底。再想想他仅仅八年,居然就在笒川经营出了偌大一份家业,粗略算算,足有二三万两,难不成他真是个商业奇才?
事到如今,管事汉子又收了他们的钱,自然不好意思装傻充愣,撒手不管。见他们要求“去看看”,也只好牵了匹马,头前带路。
虽只是五月初,天气已然渐热,但走在绿珠沟里,周围都是搭起的葡萄架子,葡萄枝蔓攀延,一片片碧绿叶子像小蒲扇般层层叠叠铺盖,风一吹过,叶子碧涛般起伏涌动,密密的枝叶间涌出阴凉潮润的气息,扑在脸上,顿时暑意全消,让人精神一振。葡萄架下,还不时转出正在劳作的年轻姑娘,一个个都有着鲜亮红润的脸庞,乌溜溜的眼珠往他们身上一转,又嘻嘻说笑着隐入枝叶间了。
走了半个多时辰,四周渐渐荒凉。再往前,就看到山崖壁上开着一扇扇半圆门洞,都是厚重的对开木门,清一色用铁链大锁锁着。
管事汉子按照册子上登记的编号一路寻找,这一带果然呈现出年久荒芜的模样,杂草丛生,地面也是凹凸不平。
找了大概一顿饭的工夫,管事汉子“啊”了一声,立在一扇门前,抬头看看,再低头瞧瞧册子,显是找到了。
他们几人应声跟上,只见那扇木门上的漆色都剥落得差不多了,坑坑洼洼的全是风雨侵蚀的痕迹。同样也是缠着铁链,连同悬着的一把大锁都早已锈迹斑斑。
管事汉子见谭玄上前伸手,竟是欲要推门,连忙阻止:“哎哎哎,客官,说好就是看看的嘛!您这既无契书又无钥匙的,可不能强闯啊,这可使不得!”
谭玄却回头冷冷地睥睨着他,从腰间摘下一块牌子往他面前一晃,沉声道:“朝廷查案,没你的事了,休要多言!”
管事汉子心中一憷,难怪觉得这些人形容举止非同一般,原先还以为是京城来的富商,没想到竟是朝廷命官?可是这也就是他们自称,他上哪对质去?他的职责是看守管理这些酒窖,给人强闯进去,万一这酒窖主人日后来了,丢了东西查问起来,还是他的责任,到那时,上哪找这几个人去?
他有心开口请这几人留下到底哪个衙门的,姓甚名谁,为何事而来,但他只是个平头百姓,自古只有当官的盘问百姓,哪有百姓反过来盘问官家?岂不是没个眉高眼低了?他又不敢。
犹豫之间,只见那些人中似乎是为首的那个黑衣男子,已不再理会他,双手握住铁链两端,也未看他如何动作,只听“当啷”一声,铁链竟已从中间断开!
再瞟一眼他们每个人腰间都挂着的兵刃。管事汉子立刻决定老老实实闭嘴,做一个沉默是金的男人,力争完美融入身后蓬勃生长的芒草中去。
第60章
木门发出沉重的吱嘎声,一点一点地打开了。
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小小的平台,然后是一道向下延伸的阶梯。阶梯有一半平滑的坡道,可以方便用小车推送酒桶上下。
从门外洒入的天光只能勉强照到阶梯的起始,其余部分就一应湮没在沉沉的黑暗中。
不过好在门内墙壁上就插着火把,空气干燥,谭玄掏出火折子一点,居然还能用。当下便让时飞和程俊逸在门前留守,他和谢白城带着孟红菱依次走下台阶。
台阶并不长,不过十来级,走到底,面前展开的就是一个石砖铺地的长方形房间。虽尘封已久,空气却并不算陈腐,应该是在角落里留有通风孔。只是这个房间颇为深长,仅凭两支火把照不了多远。
孟红菱借着火把的光四下张望,只见这间酒窖内当真架着两排酒桶,每一只酒桶都足有半人来高。谢白城举着火把走上前去,抬手敲了敲,声音沉厚。他回头对着她和谭玄道:“竟是满的。”他举高了火把往酒窖深处照照,“这么多酒倘若变卖了,倒也该值不少钱。”
孟红菱却不关心这些。她正拼命努力的回想当年在舒夜的生活,回想当时爹爹究竟在干什么。但她想得头都痛起来了,却也没有任何印象。
她那时实在年幼,只要爹爹每天都回家,每日能吃饱穿暖,偶尔能有些新鲜玩具,就很心满意足了,哪里还会管别的事。
她再一次感到自己对父亲了解得实在太少了。他在想什么,他在做什么,他想要什么,她竟一无所知。
如果可以,她真希望可以从父亲口中亲自了解到这一切,而不是这样仿佛解谜一般苦苦追寻。
心中思绪翻飞,足下脚步却不停歇。
孟红菱跟在谭玄身后,一路往酒窖深处走去。
走了大概有十二三丈远,火光照亮了一堵墙壁。这就是尽头了。
酒桶并没有一直排到底,在酒窖的末端,留下了大概两丈见宽的一片空地。
孟红菱呆呆地望着这片被火光映照的空地,干干净净,全无一物。实在不能理解为何会这样。
他们辛辛苦苦,一路跋涉,好不容易找到这里,怎么会只找到了一堆酒桶呢?爹爹那样精心藏起的地图,把他们引到这么一个货真价实的酒窖是要做什么?
与她的震惊和茫然不同,谭玄和谢白城好像对此并无意外与失望,一个在空地上来回走着,边走边用靴底敲击着地面石砖,一个则走到墙边上,用手指挨个敲打着墙砖。
“你们这是……?”孟红菱不禁疑惑地出声询问。
“你总不会以为,你爹把要紧的东西就光明正大的摆着吧。”谭玄一边仔细体察着脚底传来的感觉,一边回答她,“既然故意留下这么一片空地,很有可能藏着什么机关。”
听他这么一说,孟红菱也觉得颇有道理,心中再度燃起希望,双手攥紧了衣摆,伸长脖子紧盯着他俩的一举一动。
见她这般紧张,谭玄不禁失笑:“放心吧,就是掘地三尺也要弄个明白的。总不能大老远的跑来喝酒吧!”
谢白城闻言笑了一声,接上道:“那你可就亏了,毕竟你又不爱喝酒。”
谭玄道:“谁说我不爱喝酒的?我只是平日里要时刻保持头脑的清醒,所以严于律己而已。”
谢白城刚想再嘲弄他两句,谭玄忽然“咦”了一声,在左边墙根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