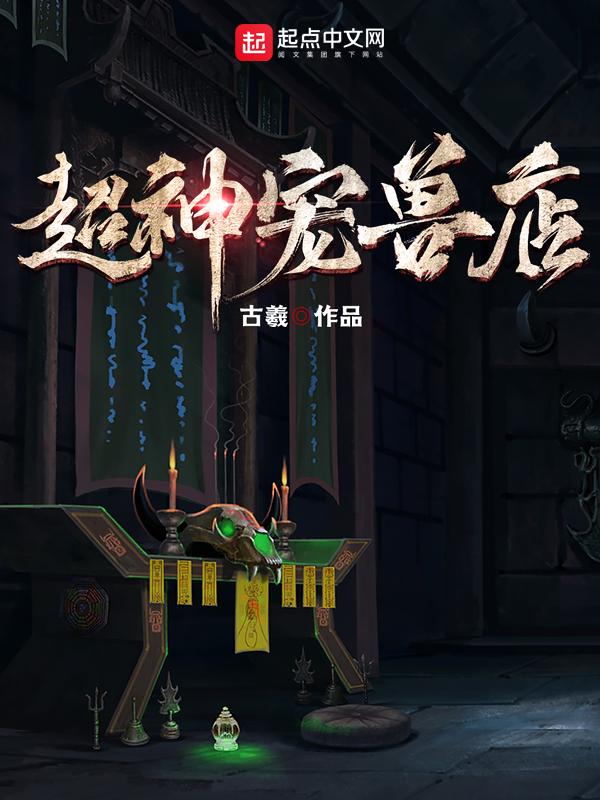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凤栖梧桐树下一句 > 第 25 章(第2页)
第 25 章(第2页)
温蘅入内,他眼皮未抬,依旧专注在眼前的字上。
温蘅也不急,静静地等他写完了字,吹干了墨,唤来狱卒将笔墨撤下,换上热茶。
他边吹气边呷了口茶,然后仿佛刚看到温蘅一般,惊讶道:“殿下怎么屈尊来此?贵足临贱地,叫微臣好生惶恐。”
嘴上这样说,身体依旧稳坐太师椅,一点行礼的意思都没有。
他招呼温蘅就像招呼自家客人一般,“既然来了,喝口茶吧。这茶虽不如自家的,但比乡下野地的,总强上几分。哦,微臣疏忽,忘了殿下兴许已经喝习惯了乡下野地的粗茶,罪过罪过。”
温蘅好似听不懂话外之音,自顾自给自己斟了杯茶。
是宫里新制的三清茶。龙井为底,配以梅花、松子仁及佛手柑,采用雪水烹制而成。还得配上青花描红茶碗,方得高洁雅致之意。
这世上从来不缺赌徒。如今徐睿知虽被下狱,但皇帝并未正式下诏定罪,有不少人赌他能东山再起。此时的殷勤侍奉与其说是雪中送炭,不如说是囤货居奇,买的是他将来复起以后换自身前程的可能。
前后两世,看得多了,并没有什么稀奇。
“从宣城给徐相带了些乡下野地的特产,还望徐相不嫌弃。嫌弃也无妨,身居高位而数典忘祖的,古往今来早已有之,多您一个不多,少您一个不少。”她将食盒往前推推,“快吃吧,过了中秋就不好吃了。”
也有可能,想吃也吃不上了。
徐睿知敛起假笑,将茶碗往桌上重重一放,眯眼盯着温蘅瞧了好几刻,好像第一次看清她长啥样。
“青州历练,殿下果然长进不少。可惜啊,你高估了微臣,也低估了陛下。秋后问斩,恐怕你是等不到了。”
温蘅:“徐谓已经写了认罪状,还主动上缴了赃物赃款。”
就他写的那些罪行,抄徐家十次都足够了。
徐睿知笑着摇头,看她的眼神仿佛在看一个稚童。这个眼神,让温蘅十分不适,好像她的所有努力在他眼里不过一场游戏。
他边笑边说:“犬子愚鲁,不是个读书的料,所以微臣从来不指望他科考入翰林,走微臣的老路。但是论起人情练达,有时候微臣都自叹不如,所以微臣给他准备的是另一条路。这次的事对他倒是个好事,破除了他一定要考取功名的执念,微臣倒要多谢殿下。”
徐睿知起身走到窗下。
这间牢房的窗户比寻常牢房来的大。阳光尽情洒进来,融融落在他身上,在他身后投下一道漆黑的影子,正好笼罩在温蘅身上。
“你以为,贪墨国库,鱼肉百姓,都是我徐家徇私枉法所致,我徐睿知背着陛下首鼠两端,我徐家打着陛下的名义中饱私囊,实实在在大禮朝一大硕鼠巨蠹对吧?可是陛下当真不知吗?”
他侧身回头,眼神如冰,“陛下沉迷修道,所费甚糜,远非国库所能支撑,那他这些年敬神祭祀、塑像修观的银钱都是从哪来的?陛下需要的真是一个两袖清风的贤相吗?还是一个能替他打点好一切、让他能够专心修道的能相?如果天下太平、朝堂稳固、神眷不衰,陛下真的在意这个相姓什么,贪了多少吗?”
温蘅面上波澜不惊,手臂上已炸起层层鸡皮疙瘩。
她明白他说的另一条路指的是什么:待新帝登基后,由新帝宣调徐谓入京,顺理成章地进入新帝班底,完成徐家权力的继承。
她更明白他为何对她如此坦诚:因为他知道对她说这些完全无碍他的筹划。在他眼里,她毫无威胁。
糟糕的是,她知道,他说的都是真的。
锥心寒意从脚底升起,迅速蔓延过全身。
*
作为一国之君,顺仁有许多不足。比如过于仁弱,以至于后期宰相窃弄国柄,几乎没有他人置喙的余地;比如过于敬神,由此形成巨大的国库亏空,导致国力衰退。
但人们议论的,从来只是他的能力问题,而不是他的态度问题。
温蘅带着满身寒意走向养心殿。她终于发现,穆熙是父亲的挚友,是宽厚的长辈,却不是一个合格的国君。
养心殿内,大理寺卿曹聪正在禀事。
“贼道玉虚已经捉拿归案,实则不过一个神棍,前任观主也是被他杀害,受骗者无数,徐谓不过其中之一……耿礼文畏罪自杀,此人官声狼藉,向来阿谀谄媚,善借上峰之手为自己行便利,之前的同僚都可佐证……徐家的状词下官看过,字字泣血,览之伤怀,其实有些非他之罪,他也认上了……殿下带回的证人下官也一一问过了,其实都未见徐谓亲犯罪行,唯一与徐家有关的人是徐家的管家……对了,徐家主动上缴的所谓赃物,有些下官不敢擅自做主,还请陛下阅后示下。”
这个人温蘅记得,是徐睿知的门生。
顺仁下令将大理寺不好处置的赃物呈上。
须臾,一辆小车载着温蘅曾在徐府看过的皇帝金身,隆隆驶过宫门,驶进顺仁逐渐明亮的眼神里。
曹聪:“听说这原是徐谓打算进奉陛下的中秋贺礼。他们还在宣城为陛下立了生祠,紧邻神火观,祈求陛下与火神并肩同临,共享永生。”
顺仁皇帝看着“赃物”沉默许久,缓缓吐出四个字:“其心可嘉。”
完了。
门外的温蘅如堕冰窟,忍不住颤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