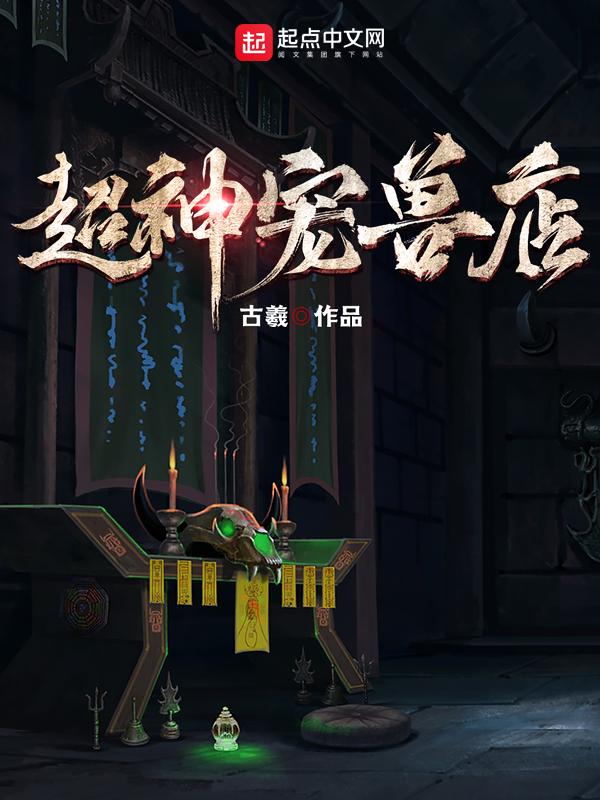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遗忘的规律是什么?如何防止遗忘? > 第 64 章(第2页)
第 64 章(第2页)
石岩掐着腰,潇洒地吹了个流氓哨,“我又不是什么柔弱不能自理的娇花弱草,哪能天天都要你来救,约好了六点三十来汇合,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她从地上捡起一只皮鞋,是陈父跑掉的,鞋垫子掉出半截,全沾了雪。
“二胎还没生出来就抓紧胎教了,受精卵学没学到位不知道,我快给听吐了。”石岩回想起每天准时响起的胎教疗愈音乐,心里很不是滋味。
贺雨行眯起眼睛,漫不经心地盯着皮鞋,刚才他全程目击了那场混战,单凭战斗力来看,那两人加起来都不够石岩一个人打的,论起逃跑,那可是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才两分钟人就跑没影了。
他学着石岩掐腰,莫名觉得这样很好看,口哨不会吹,偷偷试了两次只好放弃了,于是一本正经地问道:“他们是亲生父母吗?”
“谁知道呢,走吧,这里没我们什么事了。”石岩想起陈志豪在新世界里的模样,虽然傻是傻了点,可是挺快乐不是吗。
就不要把他再拉回来了。
石岩和贺雨行并肩走在草枚大桥上,贺雨行洒了些能量,点亮年久失修的三两盏路灯,在漫无边际的雪地上,两人踩出长长的的脚印,成串的脚印一直延伸到大桥尽头。
雪又开始下了,把昏黄的路灯染成茫茫白色,可能是弥补她没看上初雪的遗憾吧,虽然今年的初雪没看到,不过来年还有机会,如果天公作美的话。
贺雨行抖了抖头发上的雪花,静默了片刻,认真道:“我欠你一场初雪。”
“那你明年来找我还吗?”石岩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她渴望看见那种迫不及待又肯定的目光,可是贺雨行侧过脸,低垂着眼睛,眼神淡淡的,她什么也看不出来。
石岩的心冷了几分,不过还是带着笑意道:“来不了也没关系,这又不是什么要紧事,其实也算不上是你欠的,等你找到办法解除我们的能量绑定,你走了以后,到时候说不定都把我忘了。”
她踩得雪咯吱咯吱响,贺雨行也踩得咯吱咯吱响。
“会来,”他给出肯定的回答,“我不会忘了你的。”
贺雨行的话总不太多,他说什么往往直截了当,没有前面一大串的客套和铺垫,比如吃了吗、近来可好、天气如何如何诸如此类,也没有后面一大串解释,给以后的自己做不到提前找借口。
他说来,就一定会来。
说不忘,就是不忘。
石岩点头,“那我等你。”
手机开机之后,竟然有未接来电十几个,全部都来自同一个人:陈青岚。
“不会出什么事了?”石岩回拨过去,无一例外,没有一个接通。
她心里隐隐浮上一丝不安。
三天后,吕鹏程传来的消息印证了她的不安,电话那头声音暗哑,仿佛极力在憋着眼泪,“青岚走了……”
声音断断续续,停了好久,仿佛再多说一句话就要崩溃了。
这个消息太突然了,以至于石岩听完都没有任何反应,她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上一次听见陈青岚这个名字,是听说他们两个要去国外了。
怎么会。
吕鹏程发了个位置,希望石岩能来参加陈青岚的葬礼,简单来说,帮忙送葬。
“到底怎么回事?你把话说清楚。”
那头深深叹口气,声音疲惫道:“自从青岚回来以后就郁郁寡欢,说些生啊死啊的胡话,问她她什么也不说,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怎么了,都怪我没看住她,她往草枚大桥去,不知道是想不开还是不小心跌下去,总之……”
吕鹏程带着哭腔,“你们快来吧……”
电话挂断的声音在寂静的雪地中显得尤其刺耳,雪纷纷扬扬,片刻就覆盖一切痕迹,甚至就连一个完整的人,都可能悄无声息地没了。
石岩盯着贺雨行的脸,好久好久,她才说道:“我第一次参加别人的葬礼,葬礼之后,她那些生动的美好的难过的不甘的都跟着她一起入殓,人们就要忘记她了。”
不知道为什么,陈青岚那张脸慢慢清晰起来。
就连她常年的黑眼圈和鼻子上的痣也突然变清楚了。
贺雨行灰色的眸子藏在雪夜里,淡淡道:“我生生死死那么多次,没有过一次生日和葬礼。”
“生日是记忆的开始,葬礼是遗忘的开始,你想要的话,以后我给你过生日,不对应该是给你过复活日,以后你死了我就痛哭一场,然后给你欢欢喜喜地庆生。”
贺雨行听完,好像是轻轻地笑了,不过石岩没有听清,她微微抬起头看贺雨行,他望着远方的雪景,目光延伸到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