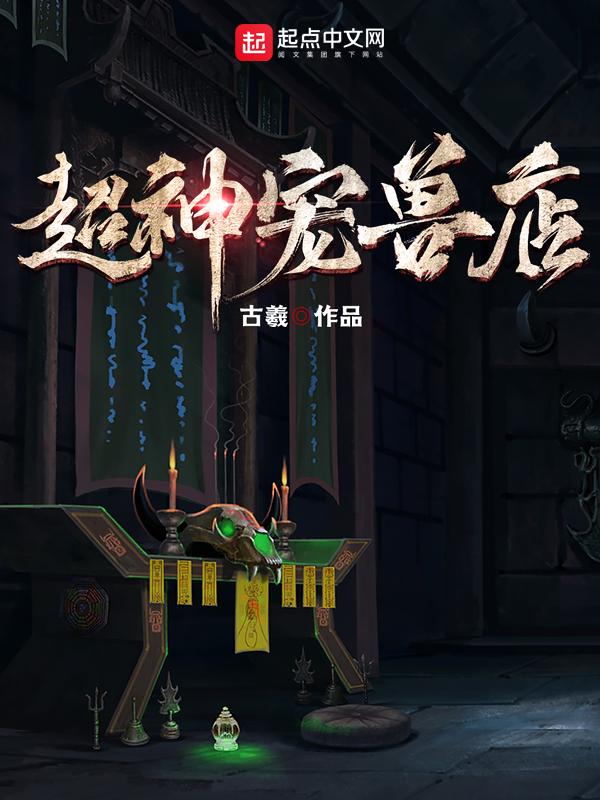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今天兄长黑化了吗?格格党 > 私通(第1页)
私通(第1页)
碗中醒酒汤的热气袅袅,熏得她眼眶有些发酸,头却越发昏沉疼痛起来。那汤药仿佛后劲十足,或许是酒意与情绪的共同作用,她的思绪渐渐变得迟缓。
她抬起头,目光迷蒙地望向裴珩,声音轻得像梦呓:“为什么要这样做?”
“招魂术,不是在折损你自己的寿命吗?”她的声音里充满了困惑和一丝哽咽咽,“何必为我做到这种地步?”
裴珩静静地看着她,看着她因酒意和困惑而泛红的脸颊,看着她眼中罕见的脆弱与迷茫。他深邃的眼底掠过一丝极为复杂的情绪,最终却归于一片沉寂。
他沉默一刻,最终只是淡淡道:“没有理由,只是想让你活下来。”
滕令欢此刻只觉得头愈来愈疼,裴璎这幅身子酒量可不好,她才没喝多少,此刻便已经有些上了头,本以为喝完醒酒汤会好一些,谁念意识居然愈发混乱。
最终她的身体软软地向一旁歪倒。
预期的冰冷坚硬并未到来,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稳固有力的怀抱。
在她彻底失去意识前,最后感知到的是一双坚实的手臂将她小心地打横抱起,鼻尖萦绕着一丝清淡的气息,混合着今夜他饮过的酒香,奇异地令人安心。
再次恢复意识时,是被窗外透进的熹微晨光唤醒的。
她缓缓坐起身,揉了揉太阳穴,昨晚的记忆断断续续地回笼,廊亭的对话、裴珩那些惊世骇俗的言语、还有最后那个不轻不重的怀抱。
她的脸颊微微发热,下意识地摇了摇头,试图将那些纷乱的思绪甩开。
起身披衣,她推开房门,清晨的冷空气扑面而来,让人精神一振。
络玉正端着一盆热水候在门外,见她出来,连忙上前,脸上带着一丝她这个年纪该有的灵动,这种表情只有她年少时的朋友拉着她说八卦才会有的。
“三姑娘,你醒了。”络玉一边伺候她洗漱,一边凑近了些,声音压得极低,“你昨晚睡得早,怕是不知道,府里后半夜可是出了大事了!”
滕令欢不解,她昨晚确实醉得突然,醒酒汤喝着喝着就没了记忆,于府中宴会后面的事确实一概不知。她接过温热的布巾敷在脸上,闻言动作一顿,从布巾下含糊地问:“什么事?”
络玉的声音更低了:“是二房的挽云姑娘,和昨晚唱戏的那个伶人,叫青烛的,”
她顿了顿,似乎及怕让人听到,环顾了一下周围,才继续道,“昨晚巡夜的马夫路过后院,见那两人赤裸着身子,在后院的假山那……”
“马夫当时被吓了一跳,引来了前厅的人,当时就闹开了,惊动了主子们,老爷带着二老爷带着人过去,挽云姑娘和那青烛被抓个正着,那青烛自觉得毁了挽云姑娘清白,当场就要撞墙自尽,好在被陈总管拦了下来,这才没让宴会上见血。”
滕令欢猛地拿下脸上的布巾,睡意和残存的酒意瞬间一扫而空,眼中满是震惊。络玉接过了那布巾,帮滕令欢洗了洗,一边洗一边说:“也不知道挽云姑娘和那青烛是怎么想的,这冰天雪地的,在后院多冷啊。”
“姑娘你不知道,你睡下后,那边院子可就乱成一锅粥了。哭喊声、斥骂声……吓死人了,这会儿还不知道怎么收场呢!”
滕令欢怔在原地,脑海里瞬间浮现出昨夜宴席上,裴挽云看着台上伶人的眼神,她早该发现的,但她当时并未深想。
谁能料到裴挽云如此大胆,竟在父亲刚刚回府、全家宴饮的当晚,就与人私会,还在裴府的后院。
裴挽云终究出身裴家,不是个不清醒的,这种事怎么可能……
莫不是被人设计陷害了?
她猛然想起昨晚后院的那一声猫叫,当时她和裴珩都在,她还要去探个究竟,但被裴珩拦住去喝醒酒汤了。
一种更深沉的寒意悄然爬上心头。
这一切,发生得太过巧合,就像有人刻意为之一般。
一股寒意从心底渗出,滕令欢只觉得四肢百骸冻得僵硬。她怔怔地站在原地,络玉后续絮叨她已经听不进去了。
她的脑海里只剩下昨夜廊亭分别前,那一声若有似无的、像是人被捂住口鼻发出的呜咽,以及裴珩将她带走时的那双眼睛。
这事实在不对劲。
那声音绝非寻常野猫,更似人声,可裴珩用一碗醒酒汤,轻易地转移了她的注意力,甚至让她昏睡过去,隔绝了后院里正在上演的一切。
一股被蒙蔽怒火涌上心头,她甚至来不及细想,身体已经先于意识做出了反应。
“络玉,我出去走走。”
丢下这句话,不顾络玉在身后的呼唤:“姑娘,早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