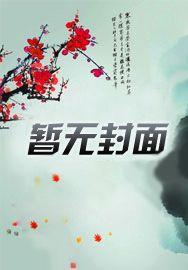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红楼之绛玉珠 > 第66章(第1页)
第66章(第1页)
“圣上恩准休沐,”宝玉挨着她坐下,拿起账册翻看,“绸缎铺的账目理得真清楚,比翰林院的文书还整齐。”他指着其中一页,“这笔胭脂水粉的开销,是给湘云那丫头垫的吧?她昨日还跟我哭穷,说月钱都买了新首饰。”
黛玉被他说中,忍不住笑:“她要去参加诗会,总得打扮体面些。再说,咱们的铺子盈利好,垫这点不算什么。”
正说着,湘云抱着个锦盒跑进来,里面是件新做的披风,湖蓝色的缎面上绣着几枝寒梅。“林姐姐!你看我做的披风!针脚是不是比上回强多了?”她得意地展开,“宝二爷说我绣的梅花像枯枝,你评评理,这明明好看得很!”
黛玉抚过披风上的梅花,针脚虽不算匀,却透着股鲜活气。“比上次的鞋垫强多了,”她故意逗她,“至少能看出是梅花,不是桃花。”引得宝玉直笑。
湘云撅着嘴把披风收起来:“我不管!诗会那日我就穿这个!对了,二姐姐和三姐姐来了,在院里赏菊呢,说要跟你讨些花籽,回去种在园子里。”
黛玉和宝玉走到院外,迎春正坐在石凳上写生,画的是株墨菊,笔尖在纸上轻轻勾勒,花瓣的纹路细腻逼真;探春则在旁边指点,手里拿着本《菊谱》,“你看这花瓣的层次,得用淡墨晕染,才显得有风骨。”
“二姐姐的画越来越好了,”黛玉走上前,看着画纸上的墨菊,“比去年菊花宴上画的更见神韵,这就叫‘熟能生巧’。”
迎春红着脸低下头:“是……是三妹妹教我用了没骨画法,说是这样更自然。”
探春笑着补充:“她如今不仅会画,还会配颜色呢,这墨菊的黑,是用松烟墨兑了点花青,才显得不发灰。”
说话间,林如海拄着拐杖走进来,身后跟着苏姨娘,手里捧着个木盒。“颦儿,你母亲留下的那套茶具,我让人修好了,”林如海打开盒子,里面是套青花瓷茶具,胎质细腻,上面绘着“潇湘夜雨”的纹样,“往后待客用这个,比寻常的体面。”
黛玉抚摸着茶杯,釉色温润,像母亲的手轻轻覆在上面。“谢谢父亲,”她眼眶微红,“我会好好收着的。”
苏姨娘笑着说:“老爷还让人在园子里搭了个暖棚,冬天也能种些时鲜菜,不像在苏州时,天冷就吃不上新鲜的。”
宝玉立刻接道:“我明日就去买些菜种,萝卜、青菜都种些,冬天就能吃你做的腌菜了,比外面买的爽口。”
黛玉白了他一眼:“就知道吃,等种出来,先给老太太和父亲送去,轮不到你先尝。”
说笑间,荣国府的嬷嬷来了,手里捧着件新做的棉袍,藏青色的杭绸面上绣着暗纹。“老太太说天凉了,让姑娘和二爷添件衣裳,这棉袍是用新弹的棉絮做的,暖和得很。还说下月初要办赏雪宴,让姑娘们都回去热闹热闹。”
“替我谢老太太,”黛玉接过棉袍,摸上去厚实柔软,“定准时回去。”
傍晚,众人坐在暖棚里吃晚饭,桌上摆着栗子鸡、腌笃鲜,还有黛玉亲手做的桂花糕。宝玉给黛玉夹了块鸡腿:“多吃点,看你最近瘦了,账册的事别太累,让账房先生多分担些。”
林如海喝了口酒,看着眼前的热闹,眼里的笑意像化了的春水。“如今这样真好,”他感慨道,“不像从前,总担心你在京里受委屈。”
黛玉握着父亲的手,又看了看身边的宝玉,心里暖烘烘的。这一世,她有父亲的疼爱,有爱人的相守,有姐妹的陪伴,像这满院的菊花,热热闹闹地开着,再没有半分孤寂。
夜里,黛玉坐在灯下,看着宝玉帮她整理账册,他的侧脸在烛光下显得格外温和。她忽然想起前世的这个时候,自己正咳得撕心裂肺,孤孤单单地守着空房,哪敢想有这般安稳的日子。
“在想什么?”宝玉抬头看她,眼里带着笑意。
“在想,”黛玉靠在他肩上,“真好。”
宝钗
小雪刚过,京城落了层薄雪,新潇湘馆的梅枝上积着雪粒,像撒了层碎玉。黛玉坐在窗边的暖炉旁,手里捧着本《女诫》,案上的青瓷瓶插着几枝蜡梅,金黄的花瓣顶着雪,香得清冽,混着炭盆的暖意,让人忘了窗外的寒。
“姑娘,宝姑娘派人送帖子来了。”紫鹃递过张粉笺,字迹端庄,说宝钗明日要过来,还带了新做的姜母鸭,说是“冬日里吃着暖身”。
黛玉放下帖子,指尖拂过“宝姐姐”三个字,嘴角漾起笑意。自她成婚后,宝钗常来走动,两人不像从前那般生分,倒多了几分姐妹的亲近。“让小厨房备些宝姐姐爱吃的糟鹅掌,再温壶上好的女儿红。”
次日午后,宝钗披着件石青色斗篷走进来,身后的丫鬟抱着食盒,里面果然是热气腾腾的姜母鸭,香气漫了满室。“妹妹近来可好?”宝钗笑着坐下,目光落在黛玉微隆的小腹上,眼里闪过欣喜,“瞧这气色,定是安稳得很。”
黛玉脸上微红,抚着小腹道:“劳姐姐挂心,太医说一切都好,就是近来总爱犯困。”
“那是自然,”宝钗打开食盒,盛出一碗鸭汤,“这姜母鸭加了当归和黄芪,补气血的,你快趁热喝。前几日我母亲寄来些闽南的桂圆,说是安胎最好,等会儿让丫鬟给你送来。”
正说着,湘云掀帘进来,手里捧着个红布包,里面是双婴儿鞋,绣着虎头纹样。“林姐姐!宝姐姐!你们看我做的虎头鞋!”她献宝似的递过来,“袭人姐姐说刚出生的娃娃穿这个,能辟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