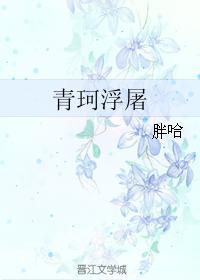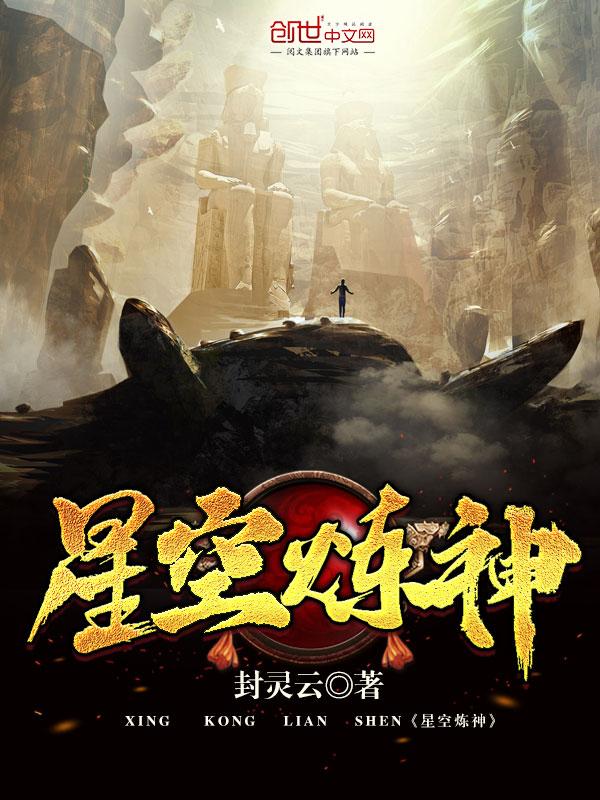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红楼之绛珠传 > 第9章(第1页)
第9章(第1页)
湘云也跟着点头:“我也帮你磨墨!我力气大,磨墨快!”
贾母见他们这般,笑着叹了口气:“你们呀,就知道凑热闹。既然玉儿愿意画,那就好好准备。鸳鸯,去把府里最好的宣纸、颜料都取来,给林姑娘送去。”
从荣庆堂出来,湘云还在念叨:“这夏太监看着就不是好人,说话阴阳怪气的。”
宝玉也皱着眉:“娘娘也是,好端端的要什么画,累着妹妹怎么办。”
黛玉看着他们护着自己的样子,心里暖暖的:“别抱怨了,不过是画幅画罢了。正好咱们可以借着看景致,在园子里多走走,也当散心了。”
接下来的几日,黛玉便开始准备画《大观园图》。宝玉果然每日都来,带着她走遍了园子里的角角落落。他记得每处景致的细节:沁芳闸桥的栏杆上雕着多少朵莲花,蘅芜院的藤萝爬了多少级台阶,稻香村的篱笆上开了几朵菊花……
黛玉把这些都记在心里,晚上就在灯下勾勒草图。紫鹃和雪雁帮着研墨铺纸,湘云有时也来,坐在一旁给她剥松子吃,说这样能提神。
宝钗听说了,也送来了些上好的颜料,是她托人从苏州带来的石青、石绿,颜色鲜亮,还不容易褪色。“妹妹画画费眼,我让人炖了些枸杞银耳汤,你记得喝。”她放下颜料,又细细叮嘱了几句,才回去了。
这日午后,黛玉和宝玉在藕香榭写生。荷叶虽已有些枯败,却另有番韵味。黛玉坐在栏杆边,手里拿着炭笔勾勒荷叶的形态,宝玉就在一旁给她扇风,时不时提醒她:“那边的芦苇再画长些,上次风吹的时候,穗子都快垂到水里了。”
黛玉笑着点头,刚要下笔,就见邢夫人身边的王善保家的带着两个小丫头过来,手里还拿着个篮子。“哟,宝二爷和林姑娘在这儿呢?”她脸上堆着笑,语气却带着几分不自在,想来是上次被王熙凤罚了,心里还记着仇。
宝玉皱眉道:“你来做什么?”
王善保家的忙笑道:“回二爷,是大太太让我来给姑娘们送些新摘的莲蓬,说是刚从园子里采的,新鲜得很。”她说着把篮子递过来,目光却在黛玉的画纸上溜了一圈,“林姑娘这是在画画?听说娘娘让您画大观园呢,真是好福气。”
黛玉没抬头,继续画着,淡淡道:“不过是些寻常景致,谈不上福气。”
王善保家的讨了个没趣,又搭讪着说了几句,见宝玉不耐烦了,才讪讪地走了。
湘云从后面绕过来,撇撇嘴:“这老婆子准没安好心,刚才我看见她在树后偷偷看了半天。”
宝玉也道:“别理她,上次的教训还没受够,还敢来这儿晃悠。”
黛玉放下炭笔,看着画纸上的荷叶,轻声道:“她来不来不要紧,咱们自己小心些便是。这画是画给娘娘的,不能出半点差错。”她知道邢夫人心里一直不待见她,王善保家的又是个爱搬弄是非的,保不齐会在画里挑什么错处。
接下来的日子,黛玉画得更仔细了。她不仅画景致,还把姐妹们平日里活动的样子也画了进去:宝钗在蘅芜院翻书,探春在秋爽斋练字,湘云在芍药栏里睡着,宝玉在沁芳闸桥边看鱼……每一笔都细细描摹,像是要把这些日子的温暖都刻在纸上。
画到一半时,黛玉有些犯愁。她想画贾母在大观园里赏雪的样子,却记不清贾母那日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裳。正在琢磨,就见贾母让人来请她去荣庆堂。
“玉儿,我听说你在画大观园?”贾母见她进来,笑着招手让她坐在身边,“我那日穿的那件石青缎子袄,你还记得吗?就是缀了珍珠扣子的那件,画上去好看。”
黛玉愣了一下,随即笑道:“老太太怎么知道我在想这个?”
贾母拍着她的手笑道:“我还不知道你?心思细得很。你尽管画,若是记不清的,就来问我,或是问你凤姐姐,她最记得这些。”
从荣庆堂出来,黛玉心里暖暖的。她忽然明白,这画不仅仅是画给元春的,更是画给这些真心待她的人的。画里的每一笔,都是她这一世的安稳与温暖。
转眼就到了九月,《大观园图》终于画得差不多了。黛玉在最后添了几笔,把潇湘馆的竹子画得更绿些,又在藕香榭的栏杆边添了只鹦鹉,正对着水面叫“林姑娘好”。
宝玉和湘云来看时,都看得直咋舌。“太像了!”湘云指着画里的自己,“这不是我上次在芍药栏里睡着的样子吗?连身上的披风颜色都一样!”
宝玉则盯着画里的黛玉,她正坐在窗边看书,竹影落在她身上,恬静得像幅画。“妹妹把自己画得真美。”他喃喃道,脸颊微微发红。
黛玉的脸也红了,嗔道:“又胡说。”心里却甜丝丝的。
次日,贾琏要进府给元春送生辰礼,黛玉便把画装裱好,让他一并带去。送画的时候,她心里竟有些舍不得,像是把这些日子的热闹与温暖都送走了。
宝玉看出她的不舍,安慰道:“不过是幅画,咱们园子里的景致还在,姐妹们也在,比画里热闹多了。”
黛玉点点头,望着窗外的翠竹,心里豁然开朗。是啊,画再好也是死的,眼前的人才是活的。这一世,她拥有的,比画里的世界要珍贵得多。
几日后,宫里传来消息,元春很喜欢那幅《大观园图》,还赏了黛玉一对玉如意,说是让她好生休养。贾母听了,喜得让厨房做了满满一桌子菜,叫了姐妹们来热闹。
席间,湘云喝了点酒,拉着黛玉的手笑道:“林姐姐,我就知道你最厉害了!连娘娘都喜欢你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