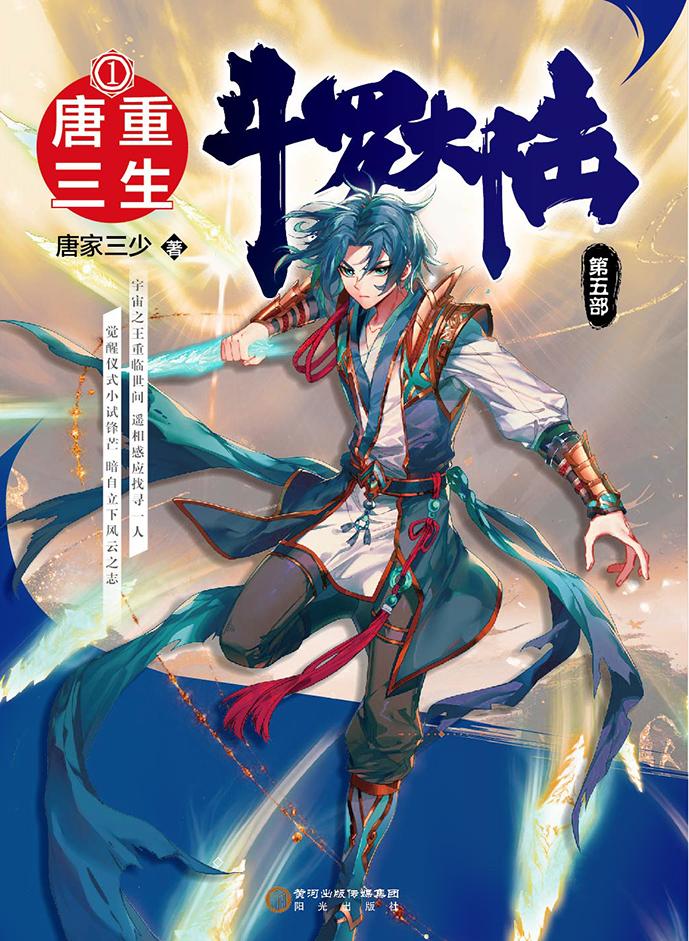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穿成男主的前妻[穿书 > 17动身(第1页)
17动身(第1页)
中午的时候,她和罗切斯特不欢而散。
他印证了一个男人的愤怒能让伴侣过得多么水深火热。
短短几个小时,她所厌恶的已经不是他的逼问,而是他把她顶到墙角时的压迫感。
她很清楚,他之所以心气不顺的原因,大概只是因为她处在他未来妻子的位置,却不符合他的期待,更不符合那个位置的规范。
因此才格外令人恼火。
她先同他告辞,回到顶层客舱,去睡她那神圣的午觉。
她裹着小毯子在床上眯了会儿,睡了不到半小时,期间还做了一个混乱的梦。
她梦见自己穿着破破烂烂、溅满血迹的婚纱,站在一个偏僻教堂的冰冷祭坛前。
她非常害怕,而且只有她自己知道是为什么,因为在那片丑陋阴暗的世界里,仿佛只有她是唯一活着的事物。
醒来后,她无法控制内心的不安,担心那将会是她不久的将来,时间在她身上踌躇不前,四周陷入了深渊般的寂静。
她想听听外面的声音。
于是,她拉开了厚重的长毛绒窗帘。
明亮的天光透过斜角玻璃照射进来。
客舱外传来音乐和人们的欢声笑语,一大群与她的命运毫不相干的乘客占领了下层甲板的露天咖啡座。
这是一个明媚的白天,船员们正在泼水清洗甲板,邮轮在清澈的海水中缓慢地行驶。
那些靠着栏杆的乘客,指着船尾浪花间忽隐忽现的鱼群与海豚,不时爆发出阵阵惊喜的欢呼。
经过漫长的独处之后,她终于能从声音中得知其他人的存在。
九月的白昼在远洋轮船上被无限拉长。茫茫大海吞噬了时间流逝的痕迹,人对时间的感知也变得越来越迟钝。
她从桌上那堆珠宝中挑出最昂贵的几件戴上,又将部分藏进暗袋,其余的仔细打包装箱。
她从容不迫地往身上堆叠着珠宝,手镯在腕间相撞发出清脆的声响,戒指在指间闪烁着明亮的冷光。
最终呈现的效果恰到好处。
既不至于浮夸到惹人怀疑,又足够彰显富贵逼人的气派。
任谁见到,都只会当这是位骄纵的富家千金在炫耀她的珍藏。
接着,她又忽然想起什么,噌的一下从地上站起,跑到卧室的衣柜前,从衬裙口袋里掏出维恩之前给她的那枚印信。
她拿着它放在手心里看了又看。
这枚刻有铭文的指环,真的能用来当做入场券,敲开拍卖会的大门吗?
总归要试一试的。
万一他送的这个东西真的无所不能呢?
她将指环紧紧攥住,眼底闪过一丝赌徒般的亮光。
最后,她又审视了一遍明早将要带走的行李。
那是一个抛光过的手提箱,自重很轻,小巧低调得不会引起任何注意。
里面整齐码放着三套简约舒服的衣物、剩余的珠宝以及那三万英镑的银行汇票。
当锁扣发出"咔嗒"的轻响时。
她抬起头,看向对面的镜墙,里面映出了一双清亮的、属于逃亡者的眼睛,正燃着一簇勇气的火焰。
她接下来的计划很清晰。
先是借那枚印信混入拍卖会,然后分批出手,先卖几件小首饰试探行情,等摸清了门路,再避开耳目将珠宝全部变现。
晚饭时分,淡紫色的峡湾上只缀着一颗星星,甲板上聚集的乘客已经散去,月光浸染海面,而她的旅程也即将开始。
罗切斯特正被几个她不认识的男人缠着品雪茄,无暇顾及她的行踪。
时机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