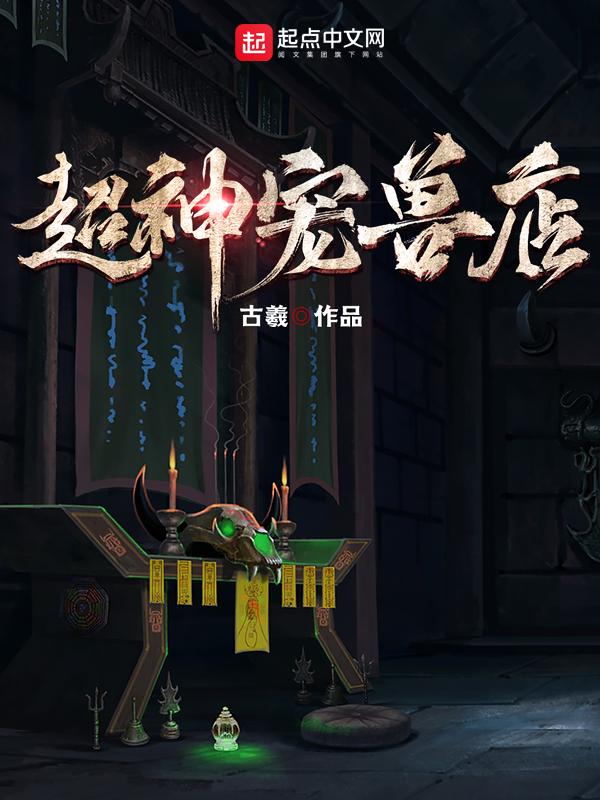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穿成男主的前妻[穿书 > 18嘶鸣(第2页)
18嘶鸣(第2页)
她弯着腰,低下头喘气,睁开眼睛环顾了下四周。
这里显然是底层甲板。
眼前的人也大多数是三等舱的乘客。
她仿佛闯入了另一个世界,从恐怖片误入了狂欢现场。
彩色的烛光在桅杆上缠绕成藤蔓的形状,威士忌酒液被泼洒在银灰色的壁板上。
黑白混血的孩童们闹哄哄地从她身边经过,人体的热气扑面而来。
对面的栏杆边,一大班水手撸起袖子敲着花纹精致的非洲鼓,身穿褪色印花裙的姑娘们正赤脚跳着吉普赛舞。
她松了口气,身后的追踪者终于消失了。
这里人多,对方肯定不能拿她怎么样。
她瘫坐在货箱边,蕾丝裙边黏在膝上。
她垂眸瞥见自己颤抖的指尖,意识到自己仍然处于一种惊魂未定的状态。
她抬起头,再度环视一圈。
微风中传来手风琴的嘶鸣,对面有个白净清秀的少年伴随着乐声吹着口哨。
这里闹哄哄的,反而驱散了她心底里的害怕和惊颤。
对面的空地上坐着一群青年,正微笑着举起手,热情地向她打招呼。
她穿着一身靓丽华服站在这里,貌美得很是惹眼。
浓褐色的甲板上人来人往,舞蹈的人影飞掠过她的身体。
她咽了一口唾沫,四肢仍然酸痛,眼前只觉得一片明亮,仿佛是在水底下睁开眼似的。
她眯起眼睛看了看天空。
深蓝色的夜幕静谧而深邃,星光灿烂,没有一丝云雾,想来明天一定会是个好天气。
她坐在墙角的长椅上,像片被浪涛抛上岸的鲑鱼,远离了大部分喧嚣,看样子疲倦得很了。
人群的声音在十步之外发酵成模糊的嗡鸣,直到一个陌生人的呼唤穿透了疲惫的屏障。
“伯莎小姐?您怎么在这儿?”
她抬起头,迷茫地看向对方。
站在眼前的陌生男人个子很高,稍微有些驼背,左眼下纹着黑山羊的削瘦头颅。
他的头发很短,是浅金色的,看起来年轻俊秀,穿着一件宽松的麻纱衬衫,白色的阔领像个伊丽莎白圈般松垮地套在他的脖颈处,被灯光映出一圈模糊的光晕。
“您不记得我了么?”
他无意识地弯腰躬身,凝神注视着她。
这过于殷勤的姿势让他看起来像一只被折弯的衣架,衬衫后背绷出一道道褶皱。
“我过去在您家当过差啊,我父亲现在还在您府上管酒窖呢!”
对方的声音里有一种熟稔的亲昵,仿佛在提醒一段本该被铭记的过往。
她的指尖微微收紧,握住了裙摆的薄纱。
她抬起头对他呆呆瞠视了一刻。
记忆像蒙尘的玻璃,无论如何擦拭都照不出清晰的影像。
她不认识这个人——至少现在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