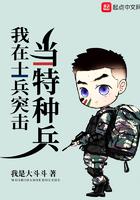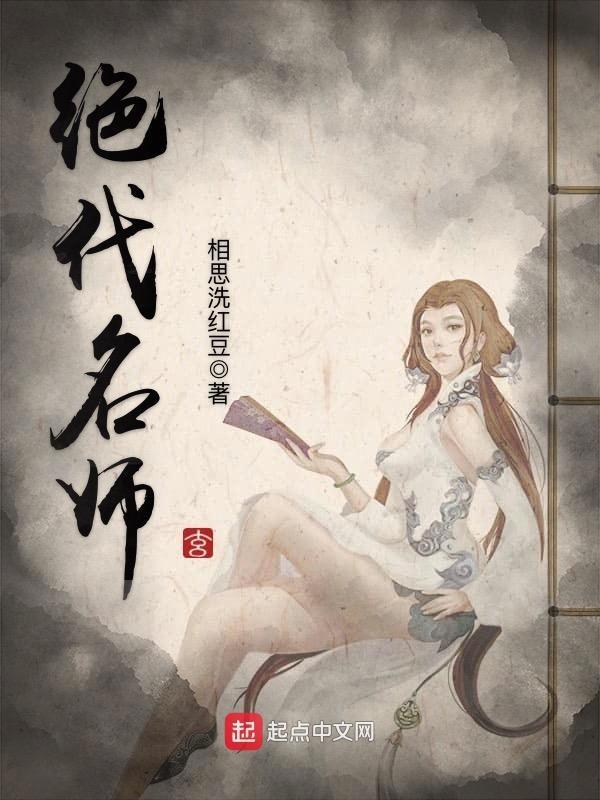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围观大唐很路人 > 15第 15 章(第2页)
15第 15 章(第2页)
李隆基闻言,以眼神示意另一个正打算出列奏事的官员先退下,他想先听听萧青梧要说些什么,或许……借此机会,又能听到什么天机呢?
【这真是个沉重又让人无奈的现实,从新石器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这几千年的时间长河中,百姓其实一直在挨饿,真正全民能吃饱饭的时间,也不过只有距离我们最近的这短短二百多年。】
【可是,这不是盛世吗……】萧青梧喃喃念着,【连京师这样的地方都在闹饥荒,那其他地方的人又该怎么办呢……】
9527虽然不是以情感交流和陪伴为主的ai,但在说到这些沉重的惨状时,它的语调也跟着调整出一些人性化的无奈:【古代所谓的盛世,也仅仅意味着饿死的人相对较少,或者大规模的饥荒得以避免,古代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能做到让大部分人都丰衣足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才是封建社会的常态。】
【整个关中都闹饥荒,这还不算大规模吗?】
【主人,古代与现代对灾害的界定标准完全不同。当前的关中粮荒,在唐代已是需要皇帝亲自应对的严重危机,但这与导致王朝覆灭、或动摇统治根基的特大灾害仍有巨大差别。总体而言,这是眼下急需解决的大麻烦,但在深度和广度上来说,规模确实不算大。尤其是唐朝灾害频发,农业生态极为脆弱,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大家对常态灾害的接受程度已经很高了。】
萧青梧听得心里越发沉重,她想起自己进宫之前,长安街头那些让人看了就不想再看第二眼的景象。
【说的也是,想一想,杜甫的儿子都能被饿死……那可是盛世啊,安史之乱还没来呢都成这样了,杜甫好歹还是个官呢……】
对啊,这不是盛世吗?为什么盛世里活着都这么难?那不是盛世的时候呢?
而一直旁听的文武百官们,脸上却十分难看,那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更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宣政殿每一个能听见她心语的人心上。
盛世……?
这两个从前总令他们骄傲的字,此刻听起来竟有几分刺耳。
他们之中,不乏出身世家大族、从未为衣食忧愁过的人,也有凭借文采与军功被重用,一路爬上来的精英。此刻,在那声声质疑中,一种混杂着不悦、轻蔑与些许被冒犯的情绪在许多人心中滋生。更有几人嘴角几不可察地下撇,心中冷哼着“妇人之言”之类的句子。
也有部分官员下意识地避开了望着上方的目光,或低头看着笏板,或望向殿外在冬日暖阳照射下的路面,脸上或多或少都带上了一丝不自在和讪讪。天灾人祸哪能避免呢?历朝历代不都是这样过来的,这次关中闹饥荒,最大的影响只是在粮价的波动上,没有到完全活不下去的地步,这、这已经很好了啊……
李隆基的脸色是其中最难看的那个,他感觉脸上火辣辣的,一股混合着羞愤、恼怒与极力否认的灼热情绪瞬间冲上他的头顶,甚至还有些自己都没察觉到的委屈。
自他登基以来,夙兴夜寐,宵衣旰食,方有今日之治世,谁敢拍着胸口说,历朝历代,有哪个皇帝的治下比他的更海晏河清?谁的百姓能如他的子民这般安居乐业?
纵然偶有天灾,也不过天道循环的常理,他数次劳师动众地巡幸东都,不正是为了纾解民困,为天下做表率吗,这次关中粮荒,他不够重视吗?他坐视不理了吗?他像杨广那样夜夜笙歌奢侈无度了吗?!
李隆基深吸一口气,缓缓压下充斥着肺腑的激烈情绪,话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他倒要继续听下去,这女人还要说些什么。
萧青梧也不负所望地继续和9527说:【那这次关中粮荒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了?很快就能过去吗?】
【去洛阳之前,李隆基向裴耀卿询问救人之策,裴耀卿建议疏浚河道,从江淮调粮至关中,并在后续工作中改革了漕运,使得关东和江淮地区的粮食大量运抵关中,大力缓解了关中的粮食压力。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按照推测,最迟到后年,关中粮食的问题能得到很大缓解。】
正支棱着耳朵听的裴耀卿一听这里面还有他的事,不由抬头望了一眼,在旁的同僚们也将目光纷纷落在他身上。
若真如这宫女所言,裴耀卿封相恐怕也不远了,毕竟,改革漕运可是大功一件。
裴耀卿自然也想到了这一点,他微微垂首,掩去眼睛里暴涨的精光,心脏不由跳得快了几分,袖子中的手都激动地攥了起来。
【不过……】众人听萧青梧又说道,【封建社会这个条件下,再怎么改革,只要动力机械一天没造出来,能改的地方就有限吧?不然为什么唐朝之后的一千多年里,远距离运粮始终是个大问题呢?】
是啊……为什么?
一些务实派的官员,如裴耀卿韩休等人,眉头锁得更紧。他们每日与漕运、仓储、田赋打交道,深知其中艰难。河道淤塞、漕船损毁、役夫艰辛、沿途损耗、地方盘剥等等……每一环都是难题。所谓的改革,往往也只是在旧有框架内修修补补,确如那女子所言,终究有其极限。
想到此,众人将目光凝在御座之后那道身影上,似乎想要看出个能解决问题的一二三来。
【您的理解完全正确,裴耀卿的改革已是当时条件下所能做到的最优解,但运输工具的动力源未有革命性突破,因此运输的成本、速度和总量存在无法逾越的上限,这是农业时代的共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