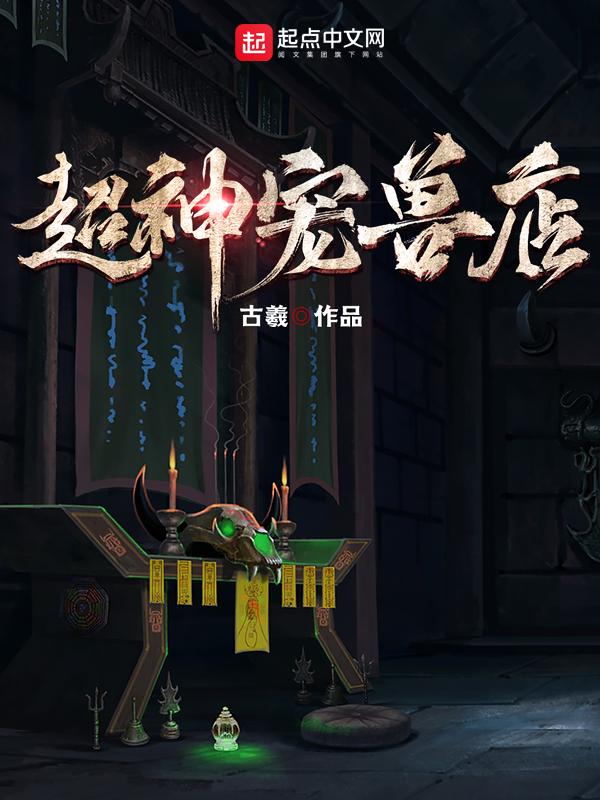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半岛玫瑰的意思 > 第97章(第2页)
第97章(第2页)
“会。”
良久,男人哑声说。
他翻身再度靠近沈续,居家服与被褥发出极其轻微的摩擦声,直至找到沈续的手,他牵住他,脚背也贴着沈续的小腿。
沈续没抵抗,一动不动,他和汤靳明很少挨得这么近,且还是和平相处。
微凉的呼吸撒在脖颈,让他想到了昨晚汤靳明掉在自己衣领里的那滴眼泪。
只是一滴,剩余的被他憋了回去。
汤靳明忍不住轻叹,低声说:“正常情况下,掩盖事实才是最明智的办法。但已经被推着走了,再想停也已经晚了。这个回答会令你失望吗。”
“不会。”
“为什么。”
“人生来性本恶,只是后期被社会道德规范才成为标杆,有这种想法很正常。就像站在顶层会有往下跳的冲动,见到可爱事物恨不得将它摧毁。汤氏的资产很难不动心,正常人都会选择更利己的那方。”
沈续抿唇,继续道:“住院部的医患关系也很复杂,患者家庭内部的纠纷更难调解。只是十几万的遗产而已,他们争得头破血流,即便老人还在病床接受治疗,也仍旧有互相推卸照顾责任,只想得到属于自己的,或者更多的继承权。十几块的验血都要计较,你手里可是整个汤氏。”
“况且。”他顿了顿:“宁心已经去世十几年,按照大众认知的常理来说,的确没必要在这个时候翻旧账,完全能等到彻底获得继承权后再下手。只是……汤连擎正盛年,等到他死的话,的确有点难度。”
“要不要等一等。”斟酌着,沈续提议道。
“你呢?”
“我?”
汤靳明睁开眼,伸出手,用指背抚了抚沈续的脸,“网民已经在知网搜索你的论文,从大学至今发表的所有,媒体八点更新的早报,半小时后论坛已经全是有关于你的帖子,你怎么不愿意等一等?”
“所以现在是九点吗?”
汤靳明无奈地将他额前碎发拢至脑后,五指穿过他的发间,至发梢:“我是问你在做这件事之前,有没有想过自己。”
已经很久没有和汤靳明这么和平地对话,沈续有点不适应,但觉得这样也很好。他看汤靳明的眼睛,汤靳明也在凝望他,这种半明不明的时候,最能让精神放松,也可以自然而然地讲出平常不敢说的。
脑海闪过与昭夏的谈话,沈续把那句转述给汤靳明:“你在监视昭夏的那段时间也没少想办法吧。”
汤靳明:“……”
沈续并不避讳昭夏那句上位者对下位的无限兼容,事实上他生活的环境就是金钱至上利益贯穿终身。
如果大喊着我不要钱,我要的是爱,这种才是真虚伪。
边脆弱边毫不手软地购入奢侈品,肆意流连酒吧,随时随地来场环球旅行,等到行程结束,才用那点微不足道的缓冲休养时间继续记起自己是需要爱,渴望亲情的孩子。
如果要用全部财富换取亲情又不乐意。
沈续摊开手,放在汤靳明眼前:“金钱事业亲情,我全部都拥有了,为什么不做让沈矔下地狱造福大众,积累功德的事情呢。”
况且。
沈续单手撑着床缘,缓缓拖着枕头靠坐在床头,冷道:“事实上我的第一个身份,沈矔的独生子,在十八岁前就已经完成。从进入医科大至今,所履行的社会责任是救死扶伤。这点对于每个对人类科学有追求的医生来说,必须贯穿终身。”
“沈矔没做到这点,反而利用技术成为加害者,所做的一切和我的人格相悖,治疗一位患者的时间很漫长,但他却能够在这期间连害无数人。”
沈续停了会,淡道:“看来比起临床治疗,送他下地狱更划算。”
“否则我治多少都不够他送走的数量。”
汤靳明看着沈续的表情,问他:“但他曾经是你追逐的目标。”
“……是啊。”沈续感叹,低着头皱眉,轻声叹息:“可惜,他已经不是我想要成为的人了。”
他曾憧憬过成为沈矔,竭力地学习他,模拟他,后来发现所有都没有意义。
其实在江城的生活,沈续多少还是有点留恋。
固然有和汤靳明相遇的原因,但更多的是让他难得过了几天看似正常的生活。
离开江城的每一秒,他都活在沈矔的光环中,这样的经历对不学无术来说的确很便利,但偏偏他想要突破父亲的挟制,能正大光明地站在人前,被当面称呼沈续,或者是沈教授之类的社会头衔。
就像昨天,他挽着施妩的胳膊,身旁簇拥着的宾客高声讨论,或低头问询,言辞间全是他这个人的信息。
沈续自认这些年严格要求自己,没什么可害怕的,既然选择暴露在大众视线下,他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