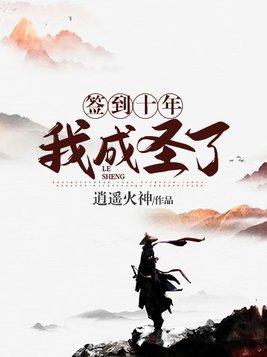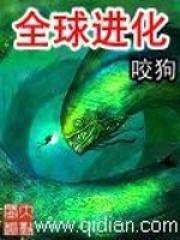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宫斗经历 > 第75章(第2页)
第75章(第2页)
在谢府简朴的客厅中,谢迁与李东阳恭敬地行礼迎接。两人面色平静,眼神清澈坚定,带着一种不容折辱的淡然。
李凤遥没有绕圈子,温和地表达了陛下与自己的挽留之意,称赞他们是国之柱石,朝廷仍需倚重。
谢迁率先开口,声音苍老却沉静:“老臣感念陛下、娘娘隆恩。然臣年已耄耋,耳聋眼花,实难再胜任阁务,尸位素餐,非人臣所为。恳请娘娘体恤,允臣这把老骨头,归葬林泉。”
李东阳亦躬身附和,言辞虽委婉,去意却同样坚决:“臣之精力,已不足以谋划国事。强留于此,于国无益,于己亦是负累。愿效仿谢公,乞骸骨归。”
李凤遥看着他们,知道挽留只是形式。她今日来的目的,也并非真心挽留。
她叹息一声,语气变得有些意味深长:“二位老先生去意已决,本宫虽不舍,亦不好强人所难。只是,二位居朝多年,门生故旧遍及天下,科举刚结束,可知这一去,天下士林会如何解读?朝野又会生出多少不必要的揣测和风波?”
她目光扫过二人平静的脸,继续道:“杨阁老为稳定朝局,弹精竭虑,有时不得不行权宜之事。陛下近日龙体欠安,本宫一介妇人,勉力支撑,所为者,不过是大明的江山社稷。若因二老离去,致使朝局动荡,人心浮动,岂非有违二老忠君爱国之本心?”
这话,软中带硬。既点明了他们辞官可能引发的后果,也将稳定的责任与他们捆绑,暗示他们的离去并非纯粹的高洁,也可能带来不安。
谢迁和李东阳何等人物,自然听懂了其中的弦外之音。两人沉默了片刻。
最终,李东阳缓缓开口,代表二人做出了承诺:“娘娘放心。臣等归野,自是闭门谢客,颐养天年,不再过问朝堂是非。朝局稳定,亦是臣等所愿。”
这就是他们能给出的最大保证,他们不会在地方上煽动舆论,不会成为反对势力的旗帜。他们会安静地离开。
李凤遥得到了想要的答案,脸上露出了恰到好处的惋惜与尊重:“既如此,本宫便代陛下,准了二老所请。愿二老一路平安,安享晚年。”
她起身,郑重地向两位老人行了一礼。
这一礼,是对他们过往功绩的承认,也是对他们最终选择的尊重,更是一种胜利者的姿态。
数日后,皇帝旨意下,恩准谢迁,李东阳致仕,赐金还乡,待遇优渥。
旨意下达之日,杨廷和在值房内独坐良久,怔怔望着对面空了的两个座位。他知道,谢、李二人这一去,所有的压力、非议与重担,将更集中地落在他一人肩上。他用自己的妥协换来的暂时平稳,终究是以牺牲了两位老友的政治生命和朝局的平衡为代价。
谢迁接到旨意,面无表情,只是对着皇宫方向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便即刻吩咐家人收拾行装,一刻也不愿在这女子乱政的朝堂多待。
李东阳接到那恩宠备至的旨意,只是淡淡一笑,对前来宣旨的中官说了许多感念天恩的场面话,转身却对着书房中悬挂的一幅旧画良久不语。那画上,是当年他与
刘健、谢迁三人共勉时的题字。
离京那日,并无多少官员敢公然相送,但许多府邸的窗口后,望着城门口带着复杂的目光。杨廷和称病未出,只派家人送去了一份程仪。
两辆简朴的马车悄然驶出京城。
马车里,谢迁闭目养神,良久,缓缓对同车的李东阳道:“西涯兄,你我今日离去,究竟是全了名节,还是将这朝堂,彻底让与了她?”
李东阳望着窗外不断后退的景物,目光幽深:“于乔兄,名节需存,然世事亦需人做。杨介夫选择了留下,他所承受的,未必比你我轻松。至于将来如何,非你我所能预料矣。”
身后,紫禁城的轮廓渐渐模糊。前方的路,通向他们陌生的田园。
两位老臣的离去,在清流士林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暗流汹涌。但表面上,朝堂却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平静。
李凤遥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以皇帝的名义,提拔了投靠她的两位资历稍浅、但更懂得审时度势、且与杨廷和关系并非铁板一块的官员入阁,悄然无声地,开始将自己的影响力更深地植入帝国的权力中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