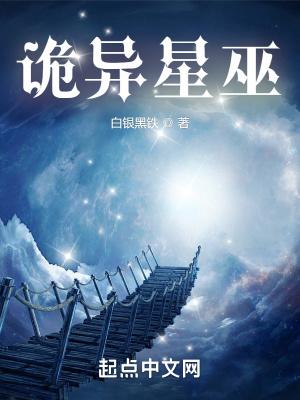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红楼皇子环 > 第6章(第1页)
第6章(第1页)
黛玉心道,一来就被给了下马威,她哪里有不难过的,在门口就忍不住眼泪了。但是顺着那为内侍哥哥指的地上的树影那么一看,抬头透过交错的树叶,看到的是一片蔚蓝而敞亮的天空,和挂在天上的太阳。
她想起苏轼的一句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凡事换个角度看,就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又如内侍哥哥说的,影子背后,有光。
她虽丧母,如今被父亲送到外祖家,二舅妈和母亲早年又有过心结。然而,外祖母疼她,一路紧紧地牵着她的手不放开;还有远在扬州的父亲对她的寄予,希望她更好地长大成人;今日遇到的三个内侍恩人,那般为她据理力争,将她从大门送入。
她不再自怜,她要好好地过。
进屋后,贾母将诸人一一指给黛玉相认。“这是你大舅母,这是你二舅母,这是你珠大嫂,你先珠大哥的媳妇。”
黛玉一一拜见。
黛玉曾听母亲说过贾家诸人。
大舅母是大舅贾赦之妻,邢氏,是续弦。邢氏忙接过黛玉,让她免礼。但见邢夫人神色复杂地看了她身边王夫人一眼,又觑了上首坐着的贾母一眼,随后抬起一双原先跟诸人一起蒙了泪光的双眼,拍了拍黛玉的双手。
黛玉见过邢夫人后,又走到王夫人跟前。
王夫人握着黛玉的手,垂泪直道苦命的孩儿,又道她苦命的小姑。贾母听到王夫人又提起她忘故的女儿贾敏,刚刚被诸人劝住了的泪眼,又淌了出来。
黛玉静静地注视着面前挂泪的王夫人,心想着,若不是今日遇到这三位仗义的内侍,若非她要被人从角门拉进来的事捅到外祖母这里,王夫人应不是看上去的这般悲怆吧。
黛玉已无泪。王夫人越是煽动气氛,黛玉越是不会再哭了。王夫人当着众人的面说她命苦,又提她亡故的母亲,还把已经不哭了的老太太又弄哭了,黛玉的心已如磐石。她看清这个家的情况了,她不会如王夫人的意,平白再让自己多增难过了。在天上的母亲,也希望她能过好。
黛玉跟王夫人见了个礼,跟刚刚对邢夫人见礼一般,礼数上不差王夫人分毫。
黛玉见过珠大嫂时,珠大嫂眼中含着的泪光却是真的,想必是想起来忘故的珠大哥吧。黛玉跟珠大嫂子伏了伏。
珠大嫂握住黛玉手,却发现黛玉小小的纤细的双手,反而将她的手握了握,像是在安慰她。珠大嫂顿生宽慰,觉得这个小姑娘好生暖心。
诸人皆对这个刚入府的小姑娘侧目。
黛玉也不知自己的心境竟然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明明刚来的时候,她还忐忑不安,谨小慎微。
所谓“一念天堂”,就是这般吧。
贾母又让把姑娘们请来,让她们今日不必上学,来见过远客。
不一会儿,迎春、探春、惜春三姐妹便被各自的乳母跟丫鬟们簇拥着来了。
黛玉跟她们互相认过,又见了礼,各自归位。
又有丫鬟斟上茶,贾母跟黛玉叙着话,说起黛玉母亲如何得病,如何请医服药,如何送死发丧。
贾母不免又感伤起来,直言道:“我这些儿女,最疼惟有你母。如今先我去了……”
说罢,贾母又搂着黛玉,呜咽起来。“如今见了你,我怎么不伤心!”
黛玉看得出来,外祖母对母亲的感情很深。她又何尝不是?
她依在慈祥的外祖母那温暖的怀中,想着今后她祖孙二人互相作伴。
众人又来劝解,贾母方略止住。
众人又喝茶叙话。忽有人问起黛玉,是不是有不足之症。又问她常服什么药?为什么不急着疗治?
黛玉坦言,打小便是有这不足之症的。家中给了请了多少名医,换过好多方剂,都不见大好。如今在吃人参养荣丸。
她想起三岁那年,家里来了个癞头和尚,说要化她出家,父母固然不从。那癞头和尚便说,这病若要好,总不许见哭声,凡有外姓亲友,一概不见,方可平安了此一生;不然这病一生也不能好的。
当时,都以为那和尚疯疯癫癫,说的都是不经之谈,没人理他。
这会儿,提到这个病,她想到曾在书中看到药王孙思邈,自幼也是体弱,但也活了一百多岁。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也是写到:“阴阳合者,必自愈。”
此时黛玉并不因诸人眼中的同情,而觉得自己命运多舛。又想到,曾有积古的老人说,江南的大家闺秀常住绣楼,缺乏运动,常有不足之症,但嫁人后不足之症便好了。便是所谓的阴阳合,必自愈。嗯……嫁人……那是很久之后的事了。
贾母说她正在配丸药,让多配一料,跟黛玉配人参养荣丸。
黛玉心道外祖母好生疼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