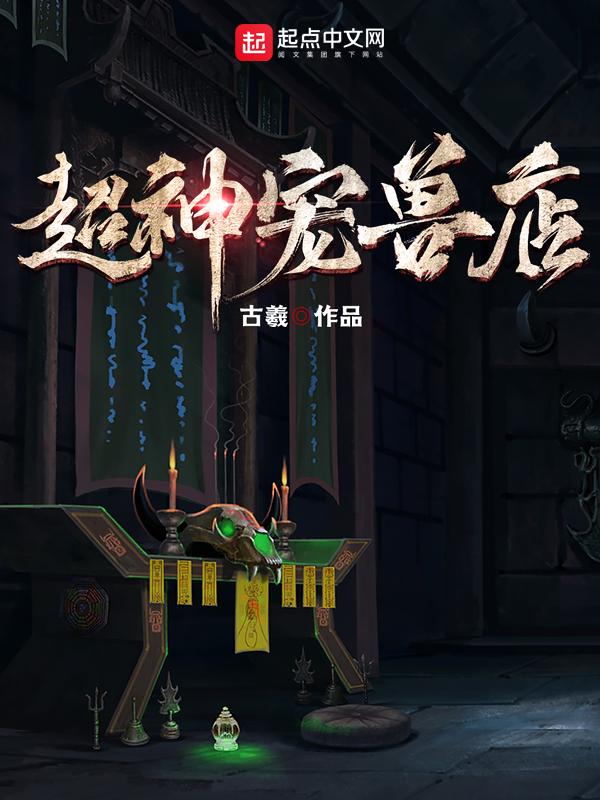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春风不度玉门关是哪首诗 > 第22章(第2页)
第22章(第2页)
“你要站起来肯定会头晕的。”张亦琦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想去搀扶。
萧翌却避开她的手,直接重重地搭在她的肩膀上,完全把她当成了拐杖,说道:“所以我才叫你过来。”
张亦琦身形单薄,不过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而萧翌已至弱冠之年,平日里又勤加习武,身材高大健硕。这一个重力压下来,张亦琦险些支撑不住,忍不住抱怨道:“殿下就不能在床上自己解决吗?”
萧翌被她这话气得笑出声来:“你当我是什么人!”
“行行行,您冰清玉洁,不食人间烟火。”张亦琦翻了个白眼,认命地当起了人肉拐杖,心里默默吐槽,这人可真矫情,看样子矫情的人从古至今都是一脉相承。上辈子在医院时,她也碰到过一些需要绝对卧床的病人,偏不听医嘱,非得下床自己去卫生间解决个人问题,结果有的人问题还没解决完,就倒在了卫生间。
张亦琦环顾四周,疑惑道:“这帐里也没有恭桶啊?”
萧翌揉了揉眉心,一脸嫌弃道:“恭桶不应该在恭房吗?”他素来极为爱洁,即便在外行军,也容不得恭桶这种秽物出现在自己日常起居的营帐里。
“那你……”张亦琦再次无奈,“你这么折腾,肺里的伤口要是又裂开可就麻烦了!”
萧翌瞥了她一眼,淡淡道:“这不是有你吗?阎王叫我三更死,你不是把我留到了五更。”
张亦琦在心里直骂,这人真的是不可理喻。
恭房位于军帐西侧,夜风裹挟着青蒿的气味,扑面而来。刚到恭房门口,萧翌突然停下脚步,冷声道:“退后十步。”张亦琦瞧着他那虚弱的身子缓缓走进帐内,心里忍不住嘀咕,要是他一会儿倒在里面,自己可绝对不会进去扶他。
没过多久,萧翌便走了出来,巡防的士兵眼疾手快,立刻端来水让他净手。萧翌站在原地,目光越过十步的距离,直直地看向张亦琦,眼神里意味深长。张亦琦假装没看懂,故意别过头去。可萧翌就这么静静地盯着她,那股无形的压力让张亦琦最终还是没扛住,只能认命地走过去,再度充当起广陵王殿下的人肉拐杖。好不容易将他扶回榻边,张亦琦开口问道:“殿下现在感觉如何?”
“无事。”萧翌神色淡淡,“你也早些歇着吧。”
“你刚刚尿量多吗?”张亦琦追问道。
萧翌深吸一口气,压抑着情绪反问:“这你也要知道?”
“当然。”张亦琦顿了顿,又道,“如果把恭桶平均分为四成,尿量大概有几成?”
萧翌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一成半。”
张亦琦暗自思忖,这个尿量还算可以。
她伸手给萧翌搭脉,脉象虽偏快,但还算平稳。只是她仍担心会出现迟发性出血的状况,便说道:“我再等等。”随后回到案边,继续研读医书。萧翌半靠在榻边,静静地看着她,不知不觉间,也沉沉睡去。张亦琦看了一会儿书,渐渐感到疲惫,临睡前,她没忘记再给萧翌把一次脉,脉象依旧平稳,这才回到角落的小床上,和衣睡下。
晨光悄然穿透牛皮帐幕的瞬间,张亦琦猛地睁开眼睛。此时天光尚未大亮,帐中弥漫着靛青色的暗影。她盯着头顶陌生的牛皮纹路,愣神了好一会儿,才想起自己正睡在广陵王的主帐里。萧翌还保持着昨夜倚榻而眠的姿势,玄色织金蟒纹袍服在晨曦中泛着幽幽的光。张亦琦轻手轻脚地挪到榻边,正准备探他的腕脉,突然寒芒一闪,一道冷铁贴着她的颈侧划过,削断了几缕青丝,剑锋上散发着霜雪般的凛冽杀气。一把冰冷的长剑就这样架在了她的脖子上。这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二次让她产生一种大难临头、命不久矣的感觉。她像被施了定身咒一般,僵在原地,连吞咽口水时,都能感受到剑刃的微微颤动。榻上的萧翌缓缓睁眼,凤眸中还凝聚着尚未消散的戾气,待看清是她后,剑尖懒洋洋地一挑,竟将她鬓边的珠花挑落在地。
张亦琦僵在原地,过了片刻才反应过来,转身拔腿就跑。
“站住!”萧翌伸手喝道,“不是要替我把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