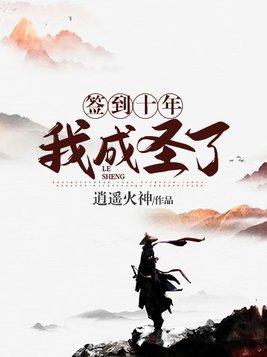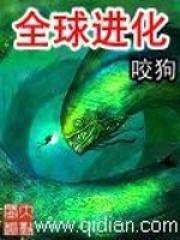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春风不度玉门关是哪首诗 > 第66章(第1页)
第66章(第1页)
王秩转过头,嘴角上扬,露出一抹自认为迷人的微笑,说道:“原来是姑娘。怎么,姑娘对我刚刚说的话有不同看法?”那语气中带着一丝挑衅,仿佛在故意找茬。
“哪有哪有。”张亦琦连忙摆摆手,脸上笑意更盛,可眼神却透着一丝狡黠,“我只是在想,要是哪天王公子遭遇不测,去往黄泉,朝廷想必也会为您超度,好给其他活人做个表率呢。”她的话语看似客气,实则绵里藏针,暗讽王秩的出言不逊。
“你!”王秩被噎得说不出话来,脸色瞬间涨得通红。
张亦琦见目的达成,心中暗自得意,微微扬起下巴,转过头去。就在这时,她的目光不经意间与主位上的萧翌交汇。一时间,她的心跳陡然加快,不知道萧翌注视她多久了,也不清楚他心中的怒火是否已经消散。
徐福悄悄靠近萧翌,压低声音,将刚刚从跟踪张亦琦的探子那里听来的消息,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他。萧翌听后,脸上的表情先是一怔,随后忍不住好气又好笑地摇了摇头。在他看来,张亦琦就是这样一个聪慧狡黠的姑娘,可对待感情却像一块不开窍的木头,让人又爱又无奈。
梵声破晓(二)
晌午,烈日高悬,炽热的光线毫无遮拦地倾洒在码头上,为那十万两官银镀上一层刺目的光。银锭表面的水渍在阳光的烘烤下迅速蒸腾,丝丝缕缕地飘散,不知为何,竟裹挟出一股腐肉般的腥气,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无端添了几分诡异。
田崇文身着绯色官袍,此刻正直直地跪在银箱前。细密的汗珠不断从他额头冒出,很快便浸湿了官袍,晕染出深色的云纹。他的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带着些难以言喻的情绪:“下官连夜审问杜远德的同党,终于在他城郊的宅邸之中寻回……”尾音落下,他喉结滚动,不知是恐惧还是兴奋,颈后青筋悄然浮起,格外醒目。
萧翌双手负于身后,快步走来,皂靴轻轻碾过青砖缝隙里半片螺壳。他忽地停下,俯身拾起一枚银锭,日光打在银子上,折射出森冷的光。“田长史可真是我朝为官的典范。”他开口,声音低沉,听不出情绪,指尖缓缓摩挲着银锭边沿的暗纹,“本王来扬州许久,都未曾寻到这十万赃银,田长史竟一夜之间就找到了。”
“殿下谬赞。”田崇文垂首,声音里带着几分谦逊,只是额上的汗珠却愈发密集。
萧翌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意味不明的笑,随即轻轻做了个手势:“徐福。”
徐福立刻快步上前,迅速走到田崇文身边,动作利落地从怀里掏出三卷布帛,依次缓缓打开。萧翌踱步上前,目光在布帛上一一扫过,悠悠说道:“田长史,这里面有你当初检举杜远德贪墨的铁证—杜远德写给漕帮的密信,信中写明,杜远德要求用废船超载运送灾民,上面还盖着他的官印。这第二份,是杜远德在狱中畏罪自杀时留下的血书。最后一份,则是杜远德在黔州任县令时所写的公文。你且看看,这三份字迹,是否截然不同?”
田崇文抬眼看向那三卷布帛,只觉眼前一黑,仿佛有千斤重负压在身上,让他说不出话来,只能机械地磕头,额头撞击地面,发出沉闷的“咚咚”声。
“这过年还早着呢,不必这么着急磕头。”萧翌哂笑一声,目光中满是嘲讽,“叶临。”
叶临上前一步,手中捧着一个木匣,递到田崇文面前:“田长史,你仔细瞧瞧,可还熟悉?”
这正是那晚萧翌和张亦琦在刺史府找到的木匣,只是萧翌已将里面两本账本收起,此刻田崇文看到的,是船底木板残骸,以及刻有他官印的调令。
“还有。”萧翌随手扔出一幅画轴,落在田崇文脚边,上面靛青绘就的水营战船暗纹,被萧翌用朱砂笔特意批注,格外刺眼。
田崇文见状,惊恐地嚎叫一声,瘫软在地,旋即大喊冤枉。
“冤枉?”萧翌冷笑一声,觉得可笑至极,“本王何处冤枉你了?人证有漕帮赖帮主,物证也一应俱全,还有这十万两赃银在此。你倒是说说,你哪里冤枉了?”
“不不不……”田崇文跪地高喊,神色慌乱,“这十万两是我自己拿出来的,并非赈灾款。”
萧翌神色冷峻,抬手敲了敲桌子,声音陡然提高:“田长史好手段啊!你不过一个扬州长史,竟能一夜之间凑足这十万两银子,这恐怕也不太合理吧?”说罢,他转头看向一旁,高声道:“扬州通判何在?”
“下官在。”通判赶忙上前,恭敬应答。
“你把昨日在衙署读给本王听的那些罪证,今日当着全扬州城百姓的面,念一念。”
“是!”通判应下,迅速拿出卷宗,开始高声宣读田崇文的罪证,房产、田产、商铺,以及贪墨的钱财,桩桩件件,清晰明了,这些都是萧翌审问杜娇妤那日,遣陆珩和许临书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