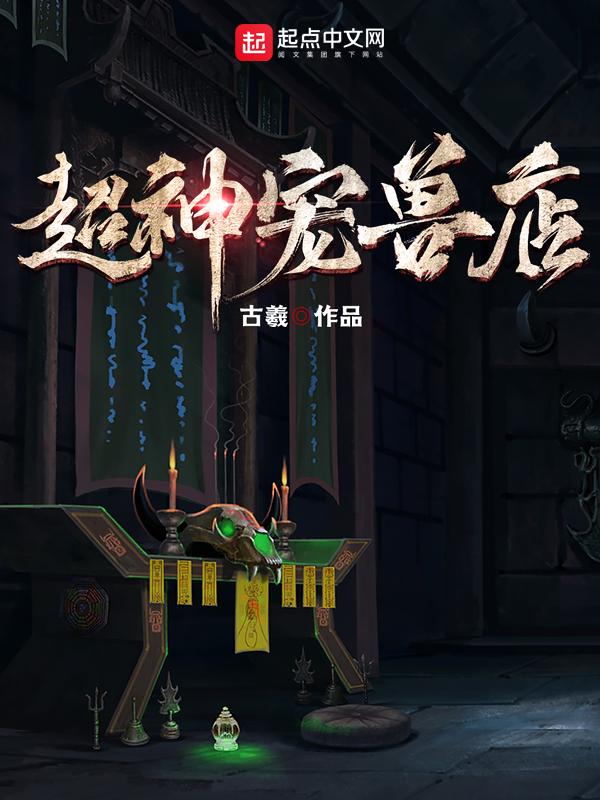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意思 > 第89章(第2页)
第89章(第2页)
张亦琦带着他去吃了点东西,听他一边哭,一边讲她走后家里的变化。
“阿姐,你走后,爹娘寻你寻了好久没寻到,后来在河边发现了一具女尸,以为是你投河了,给你埋了,又把彩礼退给了刘瘸子,可刘瘸子说我家这是骗婚,耽误了他的婚期,还弄了个死人的晦气,便狮子大开口,叫爹娘赔偿彩礼的十倍,家里哪里赔得起,刘瘸子就去县衙状告爹娘,万年县县令判我家输,还打了爹娘二十大板子,最后判了爹娘和我卖身到刘家为奴还债。”
张亦琦看着张山,昔日那个衣着虽粗布荆钗却干净妥帖的少年,已不是之前的样子,以前虽然贫苦,到也得体干净,哪像现在这般衣衫褴褛的样子。
“书不读了?”她的声音里裹着不易察觉的震颤。
张山缓缓摇头,发丝凌乱地垂在凹陷的脸颊旁。
“恨我吗?”她深吸一口气,喉间像是哽着一团棉花。
少年依然摇头,指节无意识地摩挲着衣角的破洞。
“若不是我走。。。”
“阿姐!”张山突然抬头,眼底泛起血丝,“是爹娘鬼迷心窍,非要把你嫁给刘瘸子!我去了才知道,他打死了好几个娘子!”
张亦琦望着这个在泥沼里挣扎却依然清明的少年,心中五味杂陈。纵使张氏夫妇贪婪凉薄,这株从烂泥里长出的幼苗,倒还保留着几分风骨。忽然想起张氏夫妇或许是她血脉里绕不开的根,再不堪也得伸手拉一把。
她摸出怀中金饼,“拿着,够赎你们了。往后好好读书。”
“这钱。。。”
“是我靠读书赚到的。”她避开追问,目光扫过少年惊愕的脸,“东市永宁坊何氏医馆,有事来找。”临别时,她的声音突然沉下来,”就当我死了,谁也别告诉。”
金钱赋予的底气让张亦琦的行事愈发果决。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她不想多花一分心思。
医馆里,药香与墨香交织成新的人生。她白日坐诊施药,夜晚挑灯学习,那间狭小的屋子渐渐有了人气,在这个时空漂泊了这么久,她终于再次体会到有家的感觉。
唯一不足的是她再没见到过萧翌,张亦琦第一次知道思念这个词真正的意思,当真是诗里说的,行也思君,坐也思君。那日说好了有机会就来看她,看样子这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没等到萧翌,却等到了张山来找她。不同于上次的相见,这次张山更加瘦弱了,瘦的只剩下皮包骨。
张亦琦问道”怎么了这是?”
张山崩溃大哭:“刘瘸子说卖身契是死契,钱也是他的。。。不从就往死里打。。。”
“去报官!”张亦琦拍案而起,案上茶盏剧烈摇晃。
“没用的。。。”张山绝望摇头,“他家地窖里还关着好多人。。。”
张亦琦问道“他家里有好多?不止你们三个吗?”
“不止。”
越想越觉得蹊跷,张亦琦决定和张山一起去刘瘸子家看看。
刘瘸子是刘家村的富农,虽说比不上城里的大户人家,但是在刘家村里也算是极其富裕的了。
张山还算有点脑子,找了几个最早被卖进来的,张亦琦仔细询问了原因,她发现这些被囚者无一例外来自外村——都是为天价彩礼嫁女,女儿却蹊跷暴毙,最终卖身抵债。
“他是村里一霸,没人敢惹。”那人颤抖着说。
那么这就十分耐人寻味了。
回去的路上,她仔细的回忆着,他们都是贪图刘瘸子给的高价彩礼,可怎么会这么巧,所有的女儿都是在下了聘之后再死去,有的是淹死的,有的是在树林里上吊,有的是失足摔死的。这刘瘸子专克未婚妻吗。可恨的是,这些人都以为是意外,居然没有一个想要报官,那些女子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掉了。
次日,张亦琦给张山送去一些吃的和药材,并写了一份开棺验尸同意书,她回去之后越想越觉得这件事就是个陷阱,她甚至怀疑,这些女子就是被刘瘸子弄死的。只要那些女儿的父母同意,她就可以拿着这个到县衙报案。
不一会儿,张山气喘吁吁携着文书而至,粗粝的指节上沾着未拭净的印泥。十六份联名文书边角微卷,密密麻麻的姓名下按满血红手印,另附一张牛皮纸,工笔细描着每座坟茔的方位。
张亦琦接过文书揣入袖中,直奔万年县衙。惊堂鼓被擂得震天响,铜环撞击声惊起檐下宿雀。片刻后,堂后转出个蟒袍歪斜的中年男子,玉带松垮地挂在圆滚滚的腰间,乌纱帽歪向一侧,眼角还凝着宿眠的眵目糊。
“堂下何人击鼓?”他打着酒嗝,声如破锣。
“张亦琦,为十六位不明死因的女子申冤!”
县令闻言抚掌大笑:“给死人鸣冤?当这公堂是阴曹地府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