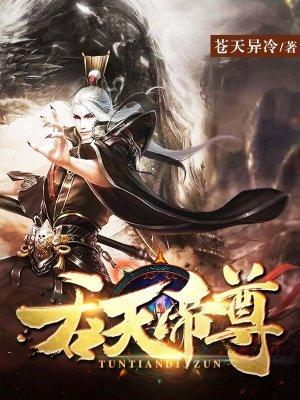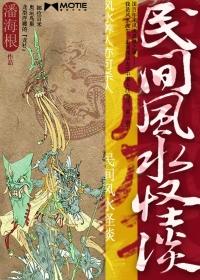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老街画画教程 > 第87章(第1页)
第87章(第1页)
李薇叹了口气:“这是文旅公司送来的方案,说要把老街打造成‘沉浸式民俗体验基地’,让张阿姨他们把摊子搬过去,统一管理,统一收费。”
“我才不去!”张阿姨端着刚和好的面团从厨房出来,脸上满是怒气,“我这馄饨摊摆了三十年,凭什么让他们管?收了钱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正说着,王师傅拄着拐杖走进来,咳嗽了两声:“刚去居委会问了,说是上面批的项目,下个月就动工。我那修鞋摊……怕是保不住了。”老爷子的声音里带着点颤抖,手里的老鞋楦被攥得发白。
画室里的气氛瞬间凝重起来。念安似乎察觉到不对劲,拉了拉林漾的衣角:“叔叔,他们要拆爷爷的摊子吗?”
林漾摸了摸他的头,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看着墙上的《修鞋摊的晨光》,画里的王师傅明明笑得那么踏实,怎么突然就要失去他守了一辈子的地方?
“不能就这么算了,”江辞突然开口,语气异常坚定,“我们去找居委会谈谈,看看能不能改改方案。老街的魂在人,在那些活生生的日子里,不是盖几间仿古建筑就能代替的。”
“谈?怎么谈?”赵宇急得团团转,“人家拿着批文呢,说是‘促进老街发展’,冠冕堂皇得很!”
“那就让他们看看,老街真正的‘发展’是什么,”林漾拿起画笔,在画纸上迅速勾勒起来,“我们把街坊们的日常画下来,把张阿姨的馄饨、王师傅的鞋楦、周老先生的画都拍下来,做成一本《老街真味》画册,送给居委会和文旅公司的人看!让他们知道,我们要的不是游客,是日子!”
江辞眼睛一亮:“好主意!还要让念安他们这些孩子也画,画他们眼里的老街,最真实!”
李薇立刻点头:“我去整理‘老街记忆’档案,把老照片、旧物件都找出来,做个临时展柜。”
张阿姨擦了擦眼角:“我现在就去包馄饨,给你们当模特!让他们看看,我这摊子不是说搬就能搬的!”
接下来的几天,社区美术馆变成了最热闹的地方。林漾和江辞带着画板,整天泡在馄饨摊、修鞋摊、周老先生的小院,把那些带着烟火气的瞬间一笔笔刻进画里;赵宇举着相机,从日出拍到日落,镜头里全是街坊们忙碌的身影——王师傅给老鞋楦上油,张阿姨在槐树下择菜,周老先生的老伴教孩子们剪纸;李薇则在展厅里搭起了临时展台,旧粮票、老算盘、磨得发亮的铜锅铲,每样东西都带着时光的温度。
念安和老街的孩子们也加入进来,用蜡笔、水彩、甚至树枝在地上画下他们心中的家。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画了幅《永不搬家的馄饨摊》,画面里的张阿姨站在老槐树下,周围飘着好多好多馄饨,像在下一场香喷喷的雨。
开展那天,居委会的人和文旅公司的负责人果然来了。他们原本带着应付的神色,可当看到展厅里的画、照片、老物件,听到街坊们七嘴八舌地讲述每个物件背后的故事时,脸色渐渐变了。
“这双鞋楦,是我父亲传下来的,”王师傅指着展台上的老物件,声音哽咽,“修了一辈子鞋,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老街的人都能穿着合脚的鞋走路。”
张阿姨端来刚煮好的馄饨:“尝尝吧,这汤是用每天现熬的骨头吊的,得守着炉子看三个钟头才行。搬去新地方,哪有这份功夫?”
负责人沉默了很久,最后拿起那本《老街真味》画册,翻到林漾画的《溪畔晨景》——画里的溪水静静流淌,溪边的老房子冒着炊烟,没有招牌,没有游客,只有过日子的踏实。
“我们再改改方案吧,”他终于开口,语气里带着歉意,“民俗体验区可以建,但不拆老摊子,不搬老店。就让新的归新的,旧的归旧的,像这溪水一样,各有各的道。”
人群里爆发出欢呼声。林漾看着江辞,对方正对着他笑,冰蓝色的眼睛里映着展厅的灯光,像落了星星。他知道,这场小小的胜利或许改变不了什么大趋势,但至少守住了老街最珍贵的东西——那些不愿被打扰的日常,那些藏在烟火里的真实。
傍晚的溪水依旧哗啦啦地淌着,夕阳把水面染成了金红色。林漾和江辞坐在溪边的石头上,看着念安和孩子们在水里捞鹅卵石,笑声像银铃一样脆。
“你看,”林漾指着远处的施工牌,“新的总要长出来,就像这溪边的嫩芽。”
“但根得留住,”江辞握住他的手,指尖的温度比春风还暖,“就像这老槐树,新枝长得再高,根还在土里。”
溪水潺潺,像在为这句话伴奏。林漾知道,老街的故事里,从此会多一道关于守护的年轮。而他们的画笔,会继续在这新旧交织的时光里游走,把每一道涟漪,都画成温柔的模样。
夏夜里的蝉鸣
入伏的夜晚,热浪像层黏腻的薄膜裹着老街。社区美术馆的吊扇慢悠悠地转着,吹不散展厅里的闷热,却把赵念安的笑声切成了细碎的片段。
十岁的小家伙正趴在长桌上,用马克笔给一幅向日葵画填色,鼻尖上沁着汗珠,却执拗地不肯开空调——“张奶奶说,吹多了空调会生病,扇扇子才舒服。”
林漾坐在旁边的藤椅上,手里摇着把蒲扇,扇面上是江辞画的水墨荷花,墨迹在反复的摇动中晕出淡淡的水痕。他看着念安笔下那朵比太阳还亮的向日葵,突然想起沈怸离开前说的那句“你比我幸运”。以前总觉得幸运在于坚守,此刻却明白,幸运是有群人陪着你,把看似固执的坚持,过成了自然而然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