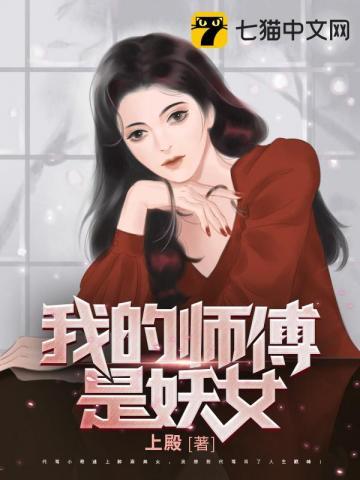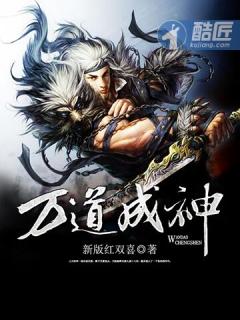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老街的画法 > 第77章(第1页)
第77章(第1页)
念安握着蜡笔,在地上乱涂乱画,歪歪扭扭的线条像条小蛇,却看得他自己咯咯直笑。林漾和江辞蹲在旁边,看着他认真的小模样,突然觉得,所谓传承,从来都不是刻意的教导,而是这样耳濡目染的瞬间——他在画里藏着爱,孩子在画外感受着暖。
下午,赵宇和李薇来接念安。赵宇一进门就举着相机:“快看我新拍的!念安抓周时抓了画笔,绝对是画画的料!”
照片里,念安坐在铺着红布的桌上,手里紧紧攥着支水彩笔,周围散落着相机、算盘、印章,小家伙却只盯着笔尖的颜色,眼神专注得惊人。
“我就说吧,”赵宇得意地扬着下巴,“随我,有艺术细胞!”
“是随林漾和江辞才对。”李薇笑着纠正他,伸手把念安嘴边的口水擦干净,“昨天他还拿着蜡笔在墙上画,画得像模像样的。”
四个人坐在向日葵丛旁的长椅上,看着念安在草地上爬来爬去,追逐蝴蝶的影子。赵宇突然感慨:“真快啊,好像昨天才在跨年夜接到他出生的电话,现在都能满地跑了。”
“可不是嘛,”李薇靠在他肩上,“等他再大点,就能帮我们整理画展了。”
林漾看着江辞的侧脸,他正低头看着念安的小脚印,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阳光穿过向日葵的花盘,在他白色的发梢上投下晃动的光斑,像撒了把碎金。
“你说,”林漾轻声问,“我们老了会不会也这样,坐在院子里看念安的孩子学步?”
“会的。”江辞转过头,眼里的光比蝉鸣还要清亮,“我们会在这里,画一辈子的老街,看一辈辈的孩子长大。”
傍晚的霞光把美术馆染成了蜜糖色,念安被赵宇扛在肩上,小手里还攥着那支蜡笔,在夕阳下挥舞着,像在指挥一场蝉鸣的交响曲。林漾和江辞收拾画具时,发现念安在地上画的“作品”旁边,多了两个小小的简笔画——一个举着画笔,一个抱着颜料盒,像极了他们俩的样子。
江辞拿出手机,把这幅“合作作品”拍下来,设成了屏保。“这是念安送给我们的第一幅画。”他说,语气里带着藏不住的珍视。
林漾看着手机屏幕,突然觉得眼眶有点热。他想起初遇时江辞冷冰冰的样子,想起巴黎街头的并肩而行,想起画室里的无数个日夜,再看看眼前的向日葵、蝉鸣、蹒跚学步的孩子,突然觉得,所有的时光都没有被辜负。
蝉鸣还在继续,向日葵还在生长,念安的笑声像串银铃,在暮色里轻轻摇晃。林漾握紧江辞的手,无名指上的向日葵戒指在霞光里闪着温润的光。
他知道,属于他们的故事,就像这画框里的时光,永远有新的色彩在添进来,永远有温暖的瞬间在发生,直到岁月把头发染白,直到画笔再也握不稳,那些藏在画里的爱,也会像向日葵的种子,在时光里生根发芽,开出新的希望。
而这漫长的故事,才刚刚走到最温柔的中段。
银杏叶上的涂鸦与时光里的回响
秋分的风卷着银杏叶掠过社区美术馆的石阶时,林漾正蹲在展厅的地板上,看着赵念安用蜡笔在画纸上涂鸦。三岁的小家伙穿着背带裤,圆滚滚的手握着支黄色蜡笔,在纸上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圆圈,非要说是“向日葵”。
“这是太阳,念念。”林漾握着他的小手,在圆圈周围加了圈锯齿状的花瓣,“向日葵要有花盘,还要有跟着太阳转的脖子。”
念安眨巴着大眼睛,突然抢过蜡笔,在“向日葵”旁边画了两个并排的小人,一个顶着爆炸头(像赵宇),一个扎着小辫子(像李薇),最后在最边上画了两个挨得极近的小人,一个画了白头发(像江辞),一个画了冲天辫(显然是林漾)。
“叔叔,阿姨,念念,花。”小家伙指着画,奶声奶气地说,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滴在画纸上,晕开个小小的黄点。
江辞端着两杯水走过来,弯腰把念安嘴边的口水擦干净:“画得真好,比你赵宇叔叔小时候画的鸡蛋还像。”他把水杯递给林漾,目光落在画上,冰蓝色的眼睛里漾着笑意,“尤其是这两个挨在一起的小人,很传神。”
林漾的脸颊有点热,伸手揉了揉念安的头发:“就你嘴甜。”
展厅门口传来赵宇的大嗓门:“小画家!你妈让你回家吃桂花糕啦!”他举着相机走进来,对着念安的涂鸦拍个不停,“这幅《全家福》必须裱起来,挂在‘成长角’c位!”
李薇跟在后面,手里拎着个食盒,里面飘出桂花的甜香:“别闹了,刚烤好的,还热乎。”她把一块桂花糕递给念安,看着他吃得满脸糖霜,无奈地摇摇头,“这孩子,随他爸,看见吃的就走不动道。”
四个人坐在银杏树下的长椅上,看着念安追着落叶跑,像只快乐的小炮弹。赵宇翻着相机里的照片,突然说:“下个月社区有亲子绘画比赛,我们带念安参加吧?就画老街的秋天,肯定能拿奖。”
“重在参与,”李薇笑着说,“别给孩子太大压力。”
林漾看着江辞低头用银杏叶拼图案——他正在拼朵向日葵,叶脉清晰的叶片叠在一起,像件精致的艺术品。“你说,”林漾轻声问,“我们第一次在复古市集买老相机,好像也是这样的秋天?”
“嗯,”江辞点头,指尖拂过叶片上的纹路,“那天你非要给我拍逆光,结果把我拍成了黑炭。”
“明明是你站得不对,”林漾不服气,“光线那么好,换个人拍都好看。”